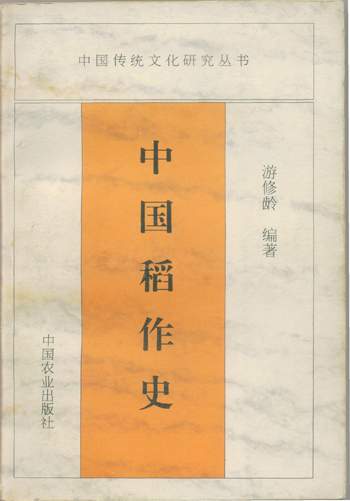
《中国稻作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游修龄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59年
序言
《中国稻作史》写写停停终于问世了。写这本书的缘起说来也是很偶然的,那是在1976年我参加了有关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的都是考古专家,因为遗址出土了大量稻谷,所以约我这个学农的参加。我也很惊讶于这么多的炭化稻谷出土,而且其年代早在7000年之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为中国的水稻(或农业)起源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虽然是农业史上的大事,对于历来公认的,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这个论点所受的冲击,才是振动全国及随之而来的世界注目的大事。
开始我只是就河姆渡稻谷作了一些鉴定和研究,写出几篇文章,谁知一脚陷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牵扯到的方面太多了,而且愈探索就愈感到问题的重要和内含的丰富。就这样,理所当然地我逐渐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中国稻作的发展历史上来。当我需要参考有关中国稻作历史各个方面的文献时,发现所需材料非常零散而稀少,只有个别的学者对水稻的起源或水稻的栽培历史作某些方面的专题研究,就其内容来看,还没有天野元之助著作中搜集和叙述的多。换言之,国内还没有稻作史的专著出版。代表中国水稻科学成就的《中国水稻栽培学》(1961),《中国稻作学》(1986)和《中国水稻》(1992)都是综述现代中国水稻科学的成就的,对于稻作的历史只能以一章的篇幅给以简单的介绍。这样,就显得稻作对于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及她周边的国家,其所产生的影响和贡献都潜伏不见了,这是多么的遗憾。
为了准备稻作史的材料,在随时注意搜求文献中的一鳞半爪外,同时开展了一些专题的研究,用现代农业科学的知识去分析鉴別在文献阅览中存在的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便有了构筑框架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的另一本《稻作史论集》。但是这与写稻作史是完全不同的事,它要求用农业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叙述,又不是也不可能按机械的历史编年排列。稻作史也不应是简单的史料铺陈,更应该充实的是它的科技发展的轨迹,而这种发展轨迹是被隐藏在文字的背后了。为此,我采取的方式是把历史和农业科技史相结合,不同的章节作不同的处理。比如,稻作的起源是距今数千年至万来年的事,没有文字,更不可能有纪年,主要依靠考古、作物驯化遗传、少数民族迁移、历史语言地理等多学科的探索论证,并且充满了学术争鸣的气氛,是很活跃的部分,必须单独列为第一章。内容最多的是稻的栽培历史,从整地、播种、育秧、插秧,到田间管理的中耕、除草、灌溉、排水、病虫防治、收获、稻田复种等,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将它放在第四章。作为第四章的外围基础,以古人对稻的生物学认识为第二章,而稻的品种资源在中国是众所周知的非常丰富,可算是世界之最,又有一定的文献记录,加以整理,成为单独的第三章。稻谷收获以后的贮藏和初加工属于产后的范畴,列为第五章,是第四章的延伸。
水稻虽然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主要粮食作物,但是北方也有悠久的种稻历史。北方(华北、西北、东北)种稻的特点是稻的分布极广,而种植的面积很小,而且分散,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断断续续,愈往后愈萎缩,始终振兴不起来,无法同南方的稻作历史结合在一起叙述,因此第六章专列一章为“中国古代北方的稻作”。
中国传统的农业(包括水稻)从史前的原始农业起,直至19世纪中期止,基本上可以说是经验的农业,即是通过长期反复的实践,获得不断感性积累而丰富起来的经验,其所作的理论认识的提高,不是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抽象的哲理思考的结晶,有其综合宏观的可贵的一面,也无庸讳言带来先天的局限性。鸦片战争后,急起直追,学习西方科学的热潮带来西方实验农学对传统农业的冲击,从此开始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因而专辟“中国近代稻作史”作为第七章,其时间定在1840–1949这一阶段。从整个稻作发展的历史看,本阶段为时不长,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
以上七章已经环绕稻作本身有关的各个方面,用纵横兼顾和有分有合的办法作了叙述。但是我不认为已经完成任务,因为我觉得写稻作史不能就稻论稻,稻米作为食物虽然是第一位的,但稻所哺育的中国人的文化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是丰富多彩的,对此不应排除在稻作史以外,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研究稻作史的本身虽然是逆向倒溯的,但是回顾的目的则是为了向前看,知道如何更好地瞻望未来。因此,本书的最后用“回顾和前瞻”作为第八章结束,其中的回顾部分主要论述稻文化的影响诸方面,前瞻部分扼要论述建国以来稻作生产的成就和历史继承关系,并从这种成就推测今后的发展前景。
当我看完本书的校样,抒了一口气,觉得终于了却一件心愿。但是在重看的过程中。把自己放在读者的地位进行评价,觉得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或需要进一步补充的东西,这个缺点已不是我自己所能做的了,相信由于本书的抛砖,不久的将来会引出更为理想的稻作史问世。
最后,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农业博物馆闵宗殿研究员的支持帮助,南京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给予查阅资料的方便,本书出版过程中由于文字图片等处理的麻烦,承穆祥桐同志不厌其烦地进行编校,农业出版社在当前学术性著作要影响经济效益的情况下,仍旧给以大力支持出版,在这里允许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游修龄
于杭州浙江农业大学农史室
199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