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家庭生计
第四节 其他农家与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状况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同样,在任何时代,家庭之间的经济水平和生活状况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唐朝把城乡居民分成九等。九等广虽然不完伞是按照财产划分,户与现代的家庭也不一样,但基本上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家庭经济情况的一个参考。
关于唐代户等的划分,特别是户等是否包括田产问题,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户等既然按照资产划分,而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资产,所以当然包括土地。[1]第二种意见认为从文献资料考察,从来就没有说明定户等之时的资产包括土地。[2]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有关记载,发现问题其实比这两种观点都要复杂。
首先我们要明白唐朝初年定户等的本意。户等制度虽然从北朝的九品混通开始,历代都有,其主要目的也都是与赋役制度有关。但是,重点还是有所不同。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度和租庸调制度,丁口之数与受田顷亩以及租庸调的输纳都直接挂钩。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家庭的贫富状况并不完全与丁口情况一致,而且也无法直接从均田制度中反映出来。户等制度就是为了反映均田制度之外,各个家庭人户贫富状况的制度,所以,无须包括地产。此是第一点。
第二点,唐代前期均田制的情况下,土地从理论上说是国家财产,土地的还授按照丁口增减进行,不属于私家财产。所以,按照资产定户等时是不应该把从国家那里授受的土地计算在内的。
第三点,唐代前期定户等的目的,是为了排定分派差役的顺序以及租庸调之外的差科的先后,冈为在止额赋税之外,所以,富户(浮财)和多丁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3]
那么唐朝定户等究竟包括那些资产呢?我们来看被论者反复讨论的西州蒲昌县开元二十一年(733)定户等资料:
蒲昌县
当县定户
右奉处分,今年定户,进降需平,乡父老等,通状过者。但蒲昌小县,百姓不多,明府对乡城父老等定户,并无屈滞,人无怨词,皆将均平,谨录状上。
下面残留了4家的户等记载:
肆户下上户
户韩君行,年七十二,老,部曲知富,年廿九,宅一区,菜园坞舍一所车牛两乘,青小麦捌硕,禾粟肆拾硕
户宋克携,年十六,中,婢叶力,年卅五,丁,宅一区,菜园一亩,车牛一乘,字牛大小二头,青小麦伍硕,禾粟拾硕
户范小义,年廿三,五品孙,弟思权年十九,婢柳叶年七十,老,宅一区,禾粟拾硕
户张君政,年四十七,卫士,弟小钦,年廿一,白丁,赁房住(?坐),禾粟伍硕,已上并依县(后缺)
我们把以上内容整理成如下表格:
表5-11 唐朝定户家庭资产表

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就会发现,各户的财产虽然很不相称,但是,财产少的两家,丁15比较多;财产比较多的两户,都是没有成丁之家。因此,可以这样初步推测,户等的评定考虑家财和丁口两个因素。而土地的授予就暗含在丁口这个因素之中了。总之,富户与多丁是唐朝定户等的基本标准。
唐代在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度已经在理念上被放弃。两税法在定户等的原则上是要“约丁产,定两税”。当时唐代中央完全没有在全国大规模调查各家各户土地占有情况的能力,文献上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蛛丝马迹。由于唐代前期的青苗钱即所谓地税,是按照实际种植丽积来征收的税目,这样,两税法的地税和户税就分别变成了土地征收的税种和按照丁口资产所征收的税种。这两项税种的加大以及取代租庸调而成为主要的国家赋税来源,是伴随着均田制的空泛不实而自然形成的。赋税制度卜的这种变化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户等的划分中包含了丁巾的成分,而丁中又与土地的占有脱节,导致了严重的赋税不均。从唐朝官员的言沦考察,唐朝前期派役不均问题比较严重,唐代后期赋税不均现象比较突出。其原因盖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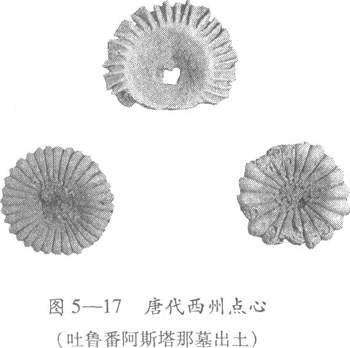
关于各个户等的实际财产情况,文献上鲜有具体记载。根据我们前面引用的吐鲁番文书中高昌县太平乡百姓的粮食贮备数字,政府要求上上户每户贮粮l5石,上中户12石,上下户10石,而中上户则为7石,最低下下户为l石。[4]这当然不是这些人家经济实力的真实反映,但是至少说明,户等高的人家是有比较多的粮食贮备的农户。实际生活中,这些农户大多有一些公共职务在身。一方面是官府把一些地方上有责任的事务交给上户人家去做,比较有经济上的保障,同时,富裕农户也一般在乡村比较有号召力。例如,唐朝初年,“置胥士七千人,取诸州上户为之”[5]。玄宗时期,富裕人户被征做诸郡的“租庸脚士”,[6]或者充当押送轻货从水路运到京城的船户。[7]乡村上户担任这些职事,一方面可以使其获得某种赋役上的减免,另一方面也使其面临很大的财产风险。
有中等就有上等和下等。农村的上户人家是: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
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群,满圈养豚子。
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多酒劝遣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却与马。
须钱便予钱,和食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
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
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
农村的极贫之家则是: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恓。两共前生种,今世作夫妻。
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
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
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裤,足下复无鞋。
丑妇来恶骂,啾唧搦头灰。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
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背)。
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漏舍儿啼哭,重重逢灾苦。
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8]
总之,农民家庭一般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属于乡村地主和比较富裕的农户,大约在户等中列入上户。一种足简单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通过土地或者其他多种经营,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还有一种,属于佃种他人的土地或者通过雇佣劳动来养家糊口的农民家庭,是最贫困的人家。从敦煌所出雇工契约可以看出,“岁作”的长工,雇价当在每月一石。另外雇主还要提供雇工个人的饮食和衣服。[9]一个雇工一年获得l2石的收入,勉强可以供给4口之家糊口,即妻子5石,年少的子女各一人共6~7石。但是,如果按照许多契约中只是正月至九月共九个月的雇约,雇工所得仅9石,还只能养活一妻一子的3口之家勉强度日。吐鲁番文书中上烽一次15天的雇价在4~10文之间,当与上烽远近有关,也与雇佣时期不同有关。[10]如果按照每文汉斗4斗计算,5文可以获得2石粮食。[11]但是,因为上烽是危险的工作,雇主且不付口粮和衣服,故所得较一般农田劳动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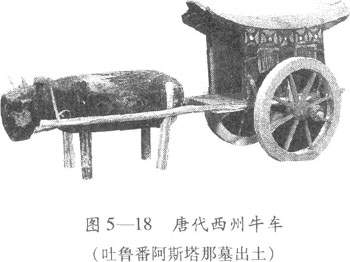
还有一些雇工实际上是一种互助和换工的性质。原因是土地资源的整合需要以及耕牛和农具的缺乏,导致了农家之间的某种互助合作形式的活动,、即使从官府请射得土地,是否有耕牛就是一个大问题。玄宗就说过一些农民“虽有垄亩,或无牛力”[12]。加上土地分散,不便耕作,于是“连畔”之地,当有互相交换土地以便耕种的可能。[13]
西嶋定生指出,西州地区的租佃文书反映出,那里由于土地授受地域分散,农民无法耕种,存在互相佃种的现象。贷主(地主)与借者(佃人)之问的经济责任和关系是平等的。这个意见得到仁井田隍的支持。池田温也从高昌m土文书的舍园买卖文书中证明这一点。[14]仁井田陞还指出,除了这种租佃关系之外,还有第二种租佃关系,即显示贷方占优势地位而借方处于劣势地位,并说这种租佃形态只见于贞观十七年(643)的文书中。
显示西州地区农民之间存在互助合作关系的还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区337号墓出土的一件龙朔三年(663)文书。[15]
龙朔三年九月十二日,武城乡人张海隆,于同乡人赵阿欢仁边,夏(假)取叁肆年中、五年六年中,武城北渠口分常田贰亩。海隆、阿欢仁二人舍佃食。其来牛麦子仰海隆边出。其秋麦二人庭分。若海隆肆年五年六年中,不得田佃食者。别(罚)钱伍拾文入张,若到头不佃田者,别(罚)钱伍拾文入赵。与阿欢仁草九围。契有两本,各捉一本。两主和同立契,获(画)指[为]记。
田主赵阿仁欢———
舍田人张海隆———
知见人赵武隆人———
知见人赵石子———
这里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拥有小块土地却缺乏耕牛和种子的农民,与缺少土地却有牛、种的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双方各自投入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共同耕作,然后均分所收获的粮食。
王梵志诗中所言的那些做雇工的极贫之家,由于还要交纳租庸,这是其极端贫困的重要原凶。否则,雇佣收入应该可以养家度日。不过这种人家虽然到处都有,但比例似乎也不大,他的观察是每村一两户的样子。当然,“广种如屯田”的“富饶田舍儿”也是少数。毛汉光先生曾经研究过西域地区农家的生活状况,认为敦煌地区在小康生活线的居民约占36%,在生存线的40%,在生存线下的占24%。吐鲁番地区在生存线的居民也是40%,但是,小康和生存线F的居民比重与敦煌调换了个,前者24%,后者36%,即总体情况比敦煌还差。[16]我们无法讨论唐代具体各个阶层农家的比例关系,何况这种比例关系不可能300年问没有变化。但是,总体而言,我想中等农家在太平的时候应该是占农家的多数的。
如果与非农家庭生计的比较,我们就发现城市居民生活其实相当不易。关于非农人家的生活状况,也可以找到一些材料。
唐于逖《灵应录》:陈太者,先家贫,贩纸为业。有一僧谓陈曰:“尔有多少口,要几许金便得足?”陈曰:“弟子幼累二十口,岁约一百缗粗备。”[17]平均每人每年5000文。相比之下,中官董秀说其家每月需钱超过千余贯,不仅是人口多、生活奢华,恐怕还有索贿的嫌疑。[18]有人献议裁汰僧道说:“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这也是像陈太这样贫穷人家的平均每人每年5000文开销的六倍。元和初,一位叫宋衍的穷举人,因病废除了明经举业,找到一份在河阴县盐铁院做书手的工作,月收入是2000文,乃“娶妻安居,不议他业”。干了一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为过三门峡的大米纲运管理账簿的差事,“月给钱八丁‘文”,却几乎因为翻船丢了性命;后来他儿子被当地节度使任为武职,获得每月5000钱的报酬。[19]这个例子表明,一个读书人找到一份抄写员的]:_=作,月人2000文,年入24000文,足可以使一般夫妻小家庭获得比较安稳的生活。月入8000文则一般是具有很大风险的职业。而一般藩镇武职可以获得月入5000的稳定收入,自然也足可以养家糊口。
城市人家的消费需求与农村有很大不同。许多东西,农村人家自己制作(如防雨器具,《四时纂要》就记载如何制作),城里人就要买。如一件防雨的油衣,根据马行街油作铺的价格表,入朝避雨衫、芭蕉裤,一副二贯。一双安州产的丝履(男用鞋),大约每双可以卖300文。[20]长安城著名的娱乐区北里,其酒席一般每桌300~400文,如果是晚席价钱就要加倍。[21]

由于城市生活处处要钱,贫民之家急于用钱,就要求助与典当。吐鲁番出土的一份质库资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该资料记载到质库借债的主要是城市居民,也有少数城郊的村妇。账历上所见到的近30人的借钱数都不大,大多只有数l‘文、百余文,最小的一笔足杨二娘用一条旧丝巾借钱20文,罕见的最大一笔为宋守慎用5件丝织品借取1800文。按照唐朝前期的长安米价水平,20文钱最多不过能买4斗米,物价贵时甚至只能买几升。借钱期限少则几天、十几天,多不过一两个月,很少超过半年以上的。说明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上往往需要一些现金,用来购买粮食或者供其他不时之需。[14]
唐人的农书说:“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为本。”[15]从以上的情况来看,以农、食为本的生活哲学,把农业当作最可靠的生业,并非古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现实因由的。
注释:
[1][日]日野开三郎即持此看法,见《唐代天宝以前にぉける土户の资产对象》,原载《东方学》17,1958年11月出版,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十一卷《户口问题匕籴买法》,(日本)三一书房l988年版,第l66页。日野先生还发表《玄宗时代を中心としてt见たゐ北支禾田地域の八、九两等户について——主として土地关系を中心に——》(载《社会经济史学》21卷5、6号,l956年4月),根据那波利贞和仁井田隍著作中提供的敦煌户籍数据考察了玄宗时代八、九等户的占田问题;认为华北地区八等户平均占田75亩左右,九等户占田45由-左右。该文又收入上书第237页。户等资产包括土地又见张泽成:《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2一12页。
[2]认为户等不包括土地的有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390页;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l995年版,第491—495页。
[3]鲍晓娜:《略论汉唐间户等与田产的关系》认为唐代定户等与田产有关系,但是,只是与私田有关系。见鲍晓娜:《耕耘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l20~129页。
[4]《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叁,第487页。
[5]《通典》卷三十五,第963页。
[6]《旧唐书》卷一百零五《王拱传》,第3229页。
[7]《旧唐书》卷叫l‘八《食货志》。
[8]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l991年版,第645—651页。
[9]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l997年版,第220~221页。
[10]吴震:《吐鲁番出土契券文书的表层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11]杨际平:《敦煌吐鲁番出土雇工契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辑,第216页。
[12]《文苑英华》卷四百六十《处分十道朝集使敕》,第2342页。
[13]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第339~340页。
[14][日]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券的一个考察》,载《西嶋定生博士还历记念·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日本)山川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296贝。
[15]关于这件史书,池田温、掘敏一都有讨论,参见[日]伊藤正彦:《七、八世纪叶鲁番的田主佃人关系》,载《中岛敏先生古稀记念论集》上卷,(日本)汲古书院l980年版,第97~124页,此处特别见第l20~121页并注26、27。
[16]项楚、郑阿财主编:《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30页。
[17]见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l76页。
[18]《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六《陈少游传》。
[19]《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宋衍》,第719~720页。
[20]见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第l41页。
[21]见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第l44页。
[22]参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贰],第328~340页;陈国灿:《从吐鲁番出土质库帐看唐代的质库制度》,载唐长孺:《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l983年版。
[23]《四时纂要序》,见唐韩鄂:《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