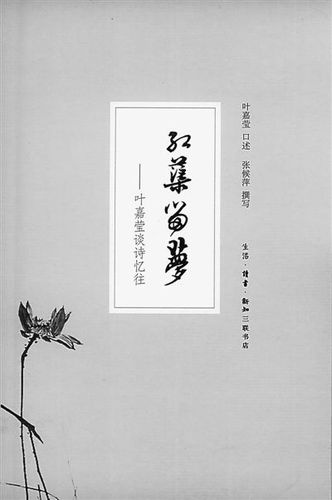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叶嘉莹
许多人因读过叶嘉莹品诗论词的文字,而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许多人因曾目睹叶嘉莹在讲台上精神矍铄的风采,从此坚信“美人不再迟暮”。然而,当我们读过《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才会明白,这位今年即将迎来鲐背之寿的老人,她有过怎样的坎坷过往,她又是如何带着近90年的沧桑与坚忍走到今天,与我们在文字中交谈、在讲堂中邂逅。
对叶嘉莹来说,逝去的是光阴,留下的是诗词,不变的是“初心”。所以当她被询及往事,“往往都是借着一些诗词旧作而追忆起来的”。叶嘉莹的求学生涯是在沦陷区的北平(今北京市)度过的,不满20岁时母亲病逝,不满30岁时在台湾因白色恐怖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被关进监狱,40多岁为在北美高校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被逼开始学习英文,50多岁又经历了丧女之痛,然而她自上世纪70年代末毅然决然开始利用假期返回祖国授课,至今未辍。一颗古典诗词滋育出的心灵,不但凭借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感发生命与人生智慧来面对人生中的穷通祸福、离合悲欢,而且又以传承古典诗词文化来实现自我超越。叶嘉莹自己说:“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研读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于是《红蕖留梦》也超越了对个人生活的津津乐道——诉说苦难时没有抱怨,表述理想时没有渲染,它似乎只是以未经磨染之“初心”在真诚地回顾一首首旧作、客观地串连起一段段往事,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在境界。这正与叶嘉莹一生无论身处何种境况内心总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强大持守力量,互为表里。
这本自传虽然是叶嘉莹的“谈诗忆往”,但因其跨度之长、经历之丰,也具有了含蓄蕴藉的诗外之味。娓娓道来的是作者对古典诗词的款款深情——从爱好者、创作者,到教学者,再到理论研究者,以至于成为一位以古典诗词学术薪传为己任的担荷者的蜕变与升华。叶嘉莹有过无家可归的境遇、咀嚼过无人可诉的孤独,甚至产生过把自己感情杀死的绝望,但今天她却被人誉为“穿裙子的士”,不仅因为她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之间、在中国经典与西方文论之间、在海峡两岸之间搭建了沟通之桥梁,更是因为她以自己的生活践行了“士人”的品格和操守,她经常称述自己从老师顾随先生所领悟的一种人生观:“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
身为旧体诗词作家,叶嘉莹的口述自传自然成为了“谈诗忆往”的追述;同时作为当代第一说诗者,叶嘉莹在《红蕖留梦》中也述及一些与其有交往的知名学者的诗词,如顾随、台静农、郑骞、李霁野、缪钺、赵朴初、陈省身、程千帆、沈祖棻、饶宗颐、陈邦炎、石声汉等,于是她充分运用自己品诗谈词时见微知著的慧眼,通过对方的诗词谈自己切实的感受,精彩纷呈,多有独得之见。《红蕖留梦》一书笔墨最多的一章是细述叶嘉莹研读治学的经历,其中首次公开披露了许多世人关注的问题,如为什么她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诗词评赏的文章不写唐宋大家而写王国维?为什么早期的文稿选用浅白的文言?为什么至今不肯写白话的抒情文字?何时从个人情感中跳出来开始完全从文学的、艺术的、批评的角度写学术论文?何时从“为己”转向“为人”的研究?何时开始了用西方文学理论探讨中国传统词学?等等。作为一个时代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学界典范,叶嘉莹有着无法复制的治学门径,所以书中谈“治学”的一章正可谓是独家秘笈,从中读者当能领悟到“初心”何以不染的个中缘由。
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教过的第一届学生毕业30周年纪念时,她深情赋诗“卅载光阴弹指过,未应磨染是初心”。这份“初心”正是叶嘉莹在《红蕖留梦》中所说的“结束的话”:“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佛家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叶嘉莹能够在承受苦难、空观悲喜后,依然执着地四海传播中国古典诗词,就在于她坚信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会中断,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生命的感动,这种感动是生生不息的。
“修辞立其诚”,这是叶嘉莹在近70年的教学生涯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今读《红蕖留梦》,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