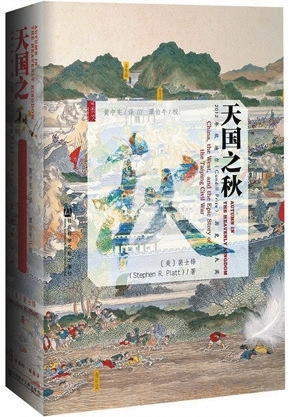
《天国之秋》,[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69.00元
历史在这里到了它最为黯淡的一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从洪仁玕抵达南京后推出的《资政新篇》等官方文件来看,在改革内政和建设新国家方面还是颇多吸收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有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气象,但外国势力的干预断送了创设这个新世界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说忠王之死,是武士之死,则干王之死,是国士之死,是中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破灭,也即希望的破灭。
1.革命,还是一场噩梦
1860年春天,太平天国主力击溃江南大营后,忠王李秀成曾经有过一项乘胜挥师东征苏、常,并进图上海的军事计划。他们的计划是拿下上海这个富庶的港口城市,再以小火轮调兵,溯长江而上,解救被湘军围困已久的上游重镇安庆。当时上海防务空虚,英法联军主力正北上进京换约,只留下千余人警戒租界,江苏巡抚薛焕能指挥的绿营主力不过三五万,上海的外围战线如此之长,从西南面的松江到西面的青浦再到西北面的嘉定,这一点点兵力,怎么抵挡得住号称十万之众的李秀成大军?
为了保住上海这座危城,革职后躲进上海做了寓公的前两江总督何桂清、上海道吴煦、买办杨坊,这些江浙系的核心人物以商会的名义聘请美国人华尔拉起了一支由各国冒险家、水手、流氓组成的雇佣军——洋枪队。李秀成不愿与洋人开战,他希望像攻取苏州一般兵不血刃拿下上海,但第一次进军上海因情报有误而受挫,随后于1862年春、夏期间连续两次发动的进攻,在洋枪队和后来开进上海的李鸿章的淮军联手阻击下也无功而返。史学界向来把李秀成三次攻打上海的失利视作晚期太平天国未能摆脱被动最终走向失败的标志性事件。
为了供养这支雇佣军,杨坊以自己的泰记钱庄运作资金,还把自己的女儿杨彰梅嫁给性格阴郁的美国人华尔,以更好地笼络住他。这桩出于利益结合的婚姻注定是脆弱的,随着华尔在浙东战场战死,新寡的杨彰梅下落不明,她的一生成谜,至今只在华尔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的一家博物馆里还保存着这个女人的少许头面首饰。
这是我的长篇新作《买办的女儿》——一段乱世烽烟中的情爱故事——展开的背景,也是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Platt)在其《天国之秋》中所约略述及的(历史学家的叙事跨度更长)。小说家感兴趣的是大时代中飘蓬般的个人命运,历史学家则要回到历史现场爬梳史料,剔除陈见,尽可能恢复事实本相。在广阔的叙事空间中,小说家和历史学家有了一次至为难得的相遇和握手,血与火、情与欲、承诺与背叛,交织成现代性降临前夜的种种曲折和波澜。最后,危巢倾覆,硝烟散去,胜利者和失败者都沉入反思:刚刚发生的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噩梦?
2013年夏天,小说写作中途,我注意到坊间出现了两部由史景迁的学生撰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即这部《天国之秋》和梅尔清的《浩劫之后:太平天国战争之遗产与19世纪之中国》,前者具全球史视野,后者从民间史和日常生活史的角度进入,都是我极欲一观的。太平天国史曾是显学,简又文、郭廷以、罗尔纲等都是大家,今则了了,好像国人都在刻意忘记这个曾经的噩梦。当时《天国之秋》尚无简体中文版,于是托一个去台湾的朋友从诚品书店购入一部繁体版。2014年岁末,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了简体中文版,只是著者斯蒂芬·普赖特不知怎的换了中文名裴士锋,正像斯蒂芬·欧文后来被称作宇文所安,写《撒马尔罕的金桃》的谢弗后来取了中文名薛爱华,大概汉学家取一个中文名也是风尚吧。
2.被干扰的历史进程
首先登场的是圆明园里孤独的咸丰皇帝;然后是香港,年轻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与落魄的客家人洪仁玕;时间快进到19世纪50年代,额尔金公爵和葛罗男爵带着庞大的英法联合舰队北上换约;然后是仇视西方势力的曾国藩的姗姗登场,忠王李秀成在上海城墙下的铩羽而归,苏、常防线冰澌雪消般的崩溃和南京最后沦陷……这针脚般密实并错综复杂的叙事,基于裴士锋这样一个观念:19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封闭体系,它已经通过贸易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了全球化的浪潮。裴士锋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审慎告诉我们,这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与世界彼端的欧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到外界的即时关注。
19世纪60年代初,东西半球各自进行着一场裹挟数千万人生命的战争。当1861年7月湘军曾国荃部攻陷安庆城屠杀数千战俘时,美国内战第一场重要战役正于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附近的布尔河畔爆发。历来很少有历史学家把发生在东西两个世界的这两场战争放在一起观照,至多也不过把它看作时间上的一个巧合。但裴士锋以全球化的独特视角发现,这两场战争对当时世界秩序的控制者英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的棉花关系着英国的纺织业,中国的茶叶则改造了英格兰的舌蕾乃至影响了英伦的生活方式。这两场同时开打的战争已经危及到了他们的经济命脉,两个经济体中任何一个的丧失,都有可能使大英帝国正蒸蒸日上的经济陷入停滞。
至此,太平天国战争已在中国南方进行达十年之久,外国势力对这场战争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中立立场。对英国政府来说,可以选择介入美国内战重启棉花贸易,但英国人认为,南北战争不论谁输谁赢,美国人还是要卖棉花的,而太平军占据沿海口岸,已经严重影响了丝茶产量及出口量。英国人现在迫切需要东方地区的稳定来维持丝茶贸易额不下降,于是他们撕下了先前一直挂着的中立者的面纱,选择了公开站在刚与之换约的朝廷一方,与之联手铰杀南方太平军。换言之,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的介入,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也正因为此,英国政治家帕默斯顿勋爵于1864年说,英国参与镇压太平军,重启中国贸易是最重要的事情,这将弥补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经济损失。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和苏、常战场上,出现了这样吊诡的一幕,刚刚在北方焚烧了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英法联军到了南方则与政府军结成了同盟,一起联手对待太平天国这个共同的敌人,把他们扭合在一起的,除了利益,别无其他。
促使华尔、戈登、法尔思德、白齐文等来自欧美的雇佣军官投身中国内战的动因,也是利益,是一个个金钱梦。攻城掠地后的巨额奖金使他们在松江、青浦、苏州等战场上如同上紧发条的疯子。但随着李鸿章率淮军取代薛焕入驻上海,“常胜军”这颗战争结成的毒瘤已注定了覆亡的命运。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战死,1863年苏州屠俘事件使戈登声誉受损,此后这支乌合之众在东部战场上已无足轻重。西方有不少传记著作过分夸大战争后期这些雇佣军官的作用,誉之“西来的战神”、“东方的劳伦斯”(裴士锋这本书也不例外),但在李鸿章等中国政治家眼里,炮灰注定是炮灰。
由此,带出了本书最为精彩的一个立论,这个论点裴士锋并未明白说出,但又无时不在场:尽管外在力量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介入中国历史进程,但它所起的并不是决定性作用,在近代的艰难转型中,中国这个巨人有它自己命定的路,任何试图借助外力改变这条道路的做法,都是一场灾难。
美国南北战争是在完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按着其历史规律走完全程的。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则不同。1909年,日本老牌政治家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英格兰人在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了太平叛乱。因为在太平天国后期,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英国人的介入使它至少苟延残喘了五十年。这样做在事实上造成“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历史进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两年后辛亥首义,满清覆亡,民国政府甫一成立,即陷入数十年内战,既印证了伊藤博文的毒舌预言,也正可以看出,这个老牛破车般的国家向着现代化的转型是何等艰难。
外国人对中国这场内战的介入,最初是非正式的、半推半就的,甚至充满道德情怀的,到后来完全站到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去,在一些外交官员、传教士和下层军官中自然会有一种道德焦虑。白齐文在华尔死后到苏州投了慕王谭绍光,又擅离太平军与戈登合作,被遣送日本后又潜回中国暗招队伍欲支援危城南京,最后在押解途中翻船溺毙,从这个人身上正可见到当时在华外国人的内心焦虑。但也有如呤唎这样的由迷惘而清醒者,这个前英国皇家海军下级军官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同情者,在1866年于伦敦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他把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一场宗教革命和民族革命,指责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干涉抱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目的。最后他选择退出,是因为他意识到,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他本人,介入这场内战都是一个错误。
3.黯淡一刻
十九世纪这场人类史上最大内战,延时十四年。屠杀和饥馑所夺走的人命,裴士锋估计为两千万至三千万。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保守估计为一千至两千万。他曾作如是描述:“人们如果穿越曾经是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五十万居民,许多河道里充斥着尸体,污物凝集。”
1861年10月,忠王李秀成与英王陈玉成合围武昌、解救安庆的军事行动失败后,忠王大军回师江浙,想重启东南战场扳回上游的失分,以范汝增一部攻取宁波——这也是天国后期惟一短期占领的出海口。当时,宁波城中基督堂的慕雅德主教曾这般描述城中乱象:“风景之美,没有能超过那些秋高气爽的十月时令,平原上深黄色的晚稻穗子一望无际,远地的冈峦起伏,气象万千,点缀着深秋花木,景色宜人,但是最凄惨不过的是,人心惴惴不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每到一村,老百姓都要问这类问题,渴望得到回答:‘长毛真的要来了吗?’‘可怕吗?’‘我们要逃吗?’”
到这场战争后半期,绿营和湘军,英法联军和雇佣军,这两股势力打着同一场战争,却都各打各的,且都自认是左右大局的惟一力量。随着雨花台外龙脖子地道的千斤火药爆炸的巨大气浪把南京城墙轰上高空,曾国藩的事业也到了他一生中最眩目的顶点。当世人惊愕地以为上天的眷顾将要落到这个湖南人身上时,这个儒家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却在破城一月后自动解散了军队,打算回老家去过他静心沉思的生活。这十几年的战争,实际上是他带领一帮儒生和乡勇护卫大清国脉之战,是一场传统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与混合着基督教、原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怪兽的卫道之战。太平天国之败,败在外侮,败在内讧,更是一场文化上的大溃败。
被选定作为胜利者的曾国藩,他对外国人的态度并不友好,他甚至本能地鄙视和排斥洋人,认为他们是未开化之人。他承认洋人机械精良,船坚炮利,但他认为道德和规训远比赢得战争重要。他的担心在于,如果清王朝允许洋人介入战争,万一洋人失败了,大清将成为笑柄;如果洋人赢了,他们必然会向中国人狮子大开口。放手让洋人介入这场战争,那就意味着中国从此要门户洞开。历史的吊诡在于,英国人出于利益考量,最终认同了鄙夷他们的曾国藩,而抛弃了对西方更加友好、更倾向于与之合作的太平天国总理政事的干王洪仁玕。洪仁玕曾在香港受过系统的基督教义熏陶,学过天文学等近代科学,有过韩山文、理雅各等不少洋人朋友,他更倾向于不与洋人冲突,而是要与西方合作,扩大贸易,分享西方的技术成果和民主平等。但最后,他寄以莫大希望的洋朋友背叛了他,也破灭了他的天堂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历史在这里到了它最为黯淡的一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从洪仁玕抵达南京后推出的《资政新篇》等官方文件来看,在改革内政和建设新国家方面还是颇多吸收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有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新气象,但外国势力的干预断送了创设这个新世界的最后一丝可能。如果说忠王之死,是武士之死,则干王之死,是国士之死,是中国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的破灭,也即希望的破灭。所以裴士锋说得好,曾国藩也罢,洪仁玕也罢,外交官、传教士、冒险家、外籍军官也罢,全都“身不由己地扮演起他们做梦都想不到而影响历史深远的角色”。
裴士锋的业师史景迁曾就太平天国史著有《天国之子与他的世俗王朝》,洋洋二十二章从太平天国的起源及兴起,摹写洪秀全的内心世界,更把重点放在太平天国宗教信仰方面。裴士锋的这本新著,依旧发挥着老师写中国史长于讲述故事的传统。在叙事策略上,除了前述全球化视角之外,他更把重点放在了战争的最后几年,亦即国际势力介入最为诡谲多变的几年,他不仅叙述了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更意在讲述中国在那个时候还可能发生什么。
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叙述总是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纠缠在一起。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对之各有不同的表述。历来官修史书称这场运动为“叛乱”,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誉之为“革命”和“起义”。裴士锋在这本书中把它命名为“内战”(civilwar),所谓内战,按国际法的惯例,是指某国之内的某种势力用武装对抗政府,而其他国家公认其为交战的一方,相对于以前界定太平天国时的“叛乱”、“起义”、“革命”等词汇,这个概念更中性、也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这场战争的力量消长。正因为裴士锋有意识撇开种种意识形态的干扰,纯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历史,《天国之秋》所起的乃是知识上祛魅的作用。这部书乃是一部祛魅之书。我的小说《买办的女儿》在叙事时间上与裴士锋颇有重合,他的历史观念对我多有启迪,在重述一个半世纪前的这段故事时,我屡屡感到我们踩在了同一个拍点上。情感的祛魅与知识的祛魅同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很愿意我写下的那个故事,也可以当作“以衰落帝国为背景,讲述良心和命运的一则道德故事”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