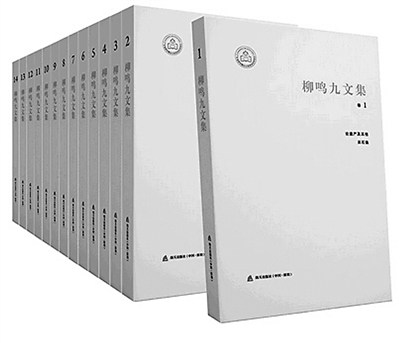
在《柳鸣九文集(15卷)》(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首发式上,我的座位正对着叠放的这皇皇巨著,心中不禁震颤起来:它凝结着我这位同事、近邻和朋友的多少心血啊!掐指一算,柳鸣九从事法国文学研究整整一个甲子了,可以说,一辈子的心血都在其中。而作为同侪,我清楚,他这辈子曾经因为各种各样不可控的因素耽误了很多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 还能有此成绩,真可谓来之不易。
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柳鸣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有战略眼光。由于“文革”中整个外国文学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就面临着如何搬掉这一“拦路虎”,“突破禁区”的问题。在这方面,“破”什么、“立”什么,是面临的首要问题。1978年秋,柳鸣九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鼓舞下,以破冰者的勇气,在广州召开的“外国文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现当代西方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公开指出了几种阻碍西方文学研究的“左”的思潮,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他一连写了三篇拨乱反正的论文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对于这三篇文章,社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的声音逐渐平息。可以说,柳鸣九在那个重要时刻的仗义执言,使他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推开大门的第一人。
西方现代主义流派林立,纷繁复杂,该从哪里入手呢?作为德语文学研究者,我自己首先抓住了现代德语文学中最有影响的卡夫卡。但初次读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主人公为了去附近的城堡开一张临时居住证而求爷爷告奶奶,我怎么也进入不了语境。洋洋23万字翻来覆去就写这么一件事情,令人费解。小说那么有名,其艺术奥秘究竟在哪里呢?不久,柳鸣九选编的《萨特研究》出版了,读了其中的小说《恶心》,觉得它的写法与《城堡》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久又读到萨特的其他著作,才对《城堡》的美学堂奥豁然开朗。存在主义文学强调写人的“生存处境”,尤其是特定境遇下的个人危机,一种火辣辣的生命感受。可以说,卡夫卡的小说是萨特和加缪存在主义哲学的最好阐释。这两人也因此成了卡夫卡的最早传播者。但萨特的思想与时俱进,他后来同情社会主义,曾数度来过中国。他提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命题、“介入社会”的人生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定义等,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他呈示的文学样式和美学主张有力地触及文学的“人学”本体,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功能,是对西方当代文学的有力推动。柳鸣九先于我们明白了这一切,并知道这些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意义,故早在1980年他就撰文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正名。不久他作为访问学者第一次去法国期间,更将萨特及其志同道合的终身女友波伏娃作为主要访问对象,回国后发表了《巴黎对话录》,和前述《萨特研究》一样,在读者中引起广泛兴趣。但就像许多最先“吃螃蟹”的人那样,由于改革开放之初各种思潮与学派的纷纭复杂,他曾一度受到质疑,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社会的发展,他的萨特缘也就渐渐变成美谈了。
柳鸣九对他的本行怀有宏大的抱负。“文革”后一恢复正常工作,他就在自己主导写就的三卷本《法国文学史》基础上,一连开启了编选三套现当代法国文学资料丛书的工程,即“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法国现当代文学资料论丛”与“西方文艺思潮丛刊”。众所周知,法国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策源地,流派迭出,思潮更迭亦快。柳鸣九的“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选了这个时期的70种书籍,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领域的各个流派和代表作家,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法国文学景观的全面呈现。起初我还想,把大量时间消耗在这类编辑性工作上是否值得?但当上述三项工程完成后联系起来看,就觉得这不仅对自身学术研究不可或缺,而且对整个学科建设亦极为必要,必将荫及后人,功莫大焉。
柳鸣九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同系但不同专业的校友,我入学的第二年,他即毕业调入当时中国科学院直属的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直到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当时的文学研究所理论力量很强,有蔡仪、毛星、陈涌等人,所长是何其芳。这期间柳鸣九受到了必要的理论训练。上世纪60年代初他提出的“共鸣说”引起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兴趣并展开讨论。这一功底使他日后的法国文学研究如虎添翼,常常一动笔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他的15卷文集除了三卷是译文外,其余12卷都是著作,这一数量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罕见的。
我一直都认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成就的大小,关键在于文学素养的高低,外语只是一个工具。前辈中较有影响的同行如钱锺书、杨绛、冯至、傅雷、李健吾、卞之琳等,哪个不是首先得益于文学?柳鸣九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也归因于此,就是说他与上述诸君一样,都属于作家型学者。这一品格使他驱逐了学术领域常见的学究气通病,赋予了他的文论以可读性较强的特色。而如果将那些占了文集一定篇幅的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独立出来,也能见出作者优秀的文学内质。如《巴黎散记》所描画的“巴黎名士”“翰林院”的“翰林”,尤其是他疼爱无比的嫡孙“小蛮女”,一般作家岂能写得出来?
一个人事业的成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天分和勤奋。有天分的人生活中并不少见,成功者或者说像柳鸣九这样的成功者却实属罕见。原因很简单:一般人不能克服天性中的惰性,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事业上。而柳鸣九却做到了这一点。这无疑需要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难怪,在电影院里几乎见不到柳鸣九的身影;单位每年春秋游,也从来没留下过他的足迹;即便像出国这样的“美差”,同行中他的频率也可能是最低的一个。这使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歌女约瑟芬,或鼠众》中的那位女主人公,她为了把她的歌唱艺术提升到“最高境界”,以“拿到那放在最高处的桂冠”,她榨干了自己身上无助于这一目标的一切!我想,也只有像柳鸣九这样有着特殊韧劲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当面对这15卷文集时,谁会说柳鸣九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所牺牲的无助于此的一切是不必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