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8月16日揭晓,格非《江南三部曲》、王蒙《这边风景》、李佩甫《生命册》、金宇澄《繁花》、苏童《黄雀记》等5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特约请5位获奖作家讲述他们的创作历程与创作理念,分享他们对文学变迁与时代脉动的观察、思考。
——编者


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
写长篇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这《江南三部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构思,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想法、新的叙事“溢”出来,但又不能推倒重来,原来的构想也舍不得放弃,所以一边写,一边寻找平衡,既回应前面的很多线索,同时又把新的异质性内容放置进去,突破和妥协都在其中。
而“溢”出来的内容又成为我手头正在写的一个新长篇的“引子”,那就是《江南三部曲》未及展开的上世纪60年代我在乡村的童年经历。告别乡村已经很久了,经过充分的记忆沉淀,现在再来讲述反而更合适。曾经的家乡现在是工业化城市中常见的“新区”,少有人提及它从宋代起就存在于长江边的历史,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
我写长篇,偏爱这些有意味的历史片段。《江南三部曲》构思之初聚焦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世纪之初这三个历史片段。每个片段都是完整的世界,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判断,很多故事只有放入历史中,和其他事件相比较,才能显出它的意义和作用来。文学超越直接描摹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往前看和往后看的视角,往前是一种想象力,往后意味着一种冷静的观察力,试图看清曾经走过的路。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往后看尤为必要,因为历史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
个人的“历史片段”未尝不是如此。回过头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新奇、冲动、走极端甚至凌空蹈虚,给我的创作打上了特立独行的印记,但也留下了过于注重技术修辞的隐患;这30年来,对普通人与普通生活的“发现”让我打破了通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观念的变化无疑会反映到创作中来,成为我个人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调整。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
当下的文学从主题、结构、语言到传播方式,产生了诸多变化。对我来说,最根本的是读写关系的变化。读者的性格、趣味、判断力日渐强势,让作家的“引导”变得困难,文学共识的获得也越来越难。这些年我自己的文学变革不是形式化、风格化的推倒重来,而是在内部悄悄地改变,为的是尊重不同层次的读者,不放弃读者。我相信,这些微小的变革同样有意义,因为好的作品会在不同层面上给予读者不同的信息和养分,伟大的作品反而往往是简单的。


王蒙:想念真正的文学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很繁荣。“文革”前17年,出版长篇小说200部,平均每年近12部。现在,纸质书加网络作品,一年数千部长篇,可多数是消费性的,解闷、八卦、爆料,还有刺激、胡诌、暴力之类。
我想念真正的文学,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实,拷问平庸与自私,发展人的思维与感受能力,丰富与提升情感,回答人生的种种疑难,激起巨大的精神波澜。真正的文学,满足灵魂的饥渴。真正的文学,读以前与读以后你的人生方向会有所区别。我相信真正的文学不必迎合,不必为印数操心,不必为误解忧虑,不必为侥幸的成功胡思乱想,更不必炒作与反炒作。
真正的文学有生命力,不怕时间的煎熬,不是与时俱逝,而是与时俱燃,火焰不熄。它经得住考验掂量,经得住反复争论,经得住冷漠对待与评头论足。不怕棍棒的挥舞,不怕起哄的浪涛。
真正的文学充满生活,充满爱情,充满关切,充满忧思与祝福。真正的文学充满着要活得更好更光明更美丽的力量。
不要听信文学式微的谣言,不要相信苛评派、谩骂派的诅咒,也不要希冀文学能够撞上大运。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是学问与思考,是创造的想象力,是自己的海一样辽阔与深邃的心。
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压了23年,1956年定稿,1979年出版第一版,但是它至今仍然在不停地重印,仍然摆在青年人的案头,仍然是阅读对象,而不仅仅是研究者的文学档案。
我的《这边风景》,初次定稿于1978年,出版于2013年,尘封了35年。作者耄耋了,书稿却比1978年时显得更年轻而且新鲜,哪怕能找出它明显的局限。
我的《活动变人形》初版于1986年,至今已经出版了29年,仍然有新的重印。
我有时发问,文学作品是像小笼包一样新出锅时滋味好,还是像醇酒一样经年发酵效果好?或者二者都是?
文学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感动,是一种对精神包容空间的开拓,是一种犀利的解剖与挖掘,还有痛彻骨髓的鞭挞。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人的度量、智慧、灵动与庄严,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人的美好或者偏狭,高尚纯洁或者矫情做作。
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是人与人、是金木水火土、是爱怨情仇死别生离、是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写作者如果一辈子生活在文学圈子里,或者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太可怜了,他们容易失眠,容易自恋,容易发狂,容易因空虚而酗酒、自杀,还容易互相嫉恨、窝里斗。
让我们更多地接地气,接天气(精神的高峰),接人气,也接仙气(浪漫与超越),接纯净的空气吧。眼界要再宽一点,心胸要再阔一点,知识要再多一点,身心要再强一些。我们绝对不能只满足于精神的消费,更要追求精神的营养、积累、提升与强化。


李佩甫:找到自己的平原
“我是一粒种子。”这是《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我曾经花了一年时间,废掉几万字,就为了找到它。我要通过这“第一句话”来决定整部作品的语言基调和情绪走向,确立这部小说的写作方向。
“平原三部曲”之间是递进关系,我期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向平原发问。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收官之作《生命册》无论从宽阔度、复杂度、深刻度来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反映了中原文化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是一次关于“平原说”的总结。
平原已经不仅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园,我的写作领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环境和领域。我的写作领地是平原。我说的平原以豫中平原腹地为根基,这里一马平川,人口密度大,无险可守,历史上灾难深重。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经人工开掘过的,到处都是人的痕迹。找到了我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我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痛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就《生命册》而言,我写的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着力于写他的“背景”、他的“土壤”。这里所说的“背景”,是指平原上一个名叫“无梁”的村庄。这个村庄是虚拟的。作品中的“我”(吴志鹏)是从无梁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从乡村一路走来,身份也一直在变,从大学老师、北漂枪手到南方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再到一家上市公司的药厂负责人……可他不是一个人在行走,他是背着一个乡村在走。他身上背负着“五千七百九十八亩土地,近六千只眼睛,还有近三千个把不住门儿的嘴巴……”他身上的每一条血管都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部长篇我采用第一人称,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切入,“以气做骨”,在结构方式上,采用分叉式的树状结构,从一风一尘写起,有枝有杈,盘旋往复。小说时间跨度很大,有50年之久,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
近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高速螺旋式的变化,常常使人目不暇接,甚至目瞪口呆。在平原,农民已逐渐演变为流动着、迁徙着的人,在大变革的潮流中被裹挟着四处奔突,过着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族、一族带一村,先漂泊后定居的复制式、印染式的生活。这是连根拔起的一种生活,是疼痛与憧憬并存的一种生活。当我们吃饱饭后,却发现大地已经满目疮痍,我们已经丧失了诗意的“家园”,人类怎么与土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再是一个老话题,也成了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新命题。


金宇澄:爱以闲谈消永昼
一部长篇从初稿到完成,到交付第一读者——出版社编辑,听取意见,再到出版,最后到获得读者的评论,这个过程一般要经过几年的时间。《繁花》走的是另一条路,从初稿五百字起,就开始接收网上不间断的读后感,一直伴随它到最后的完成。这是网络现场的魅力——写作是给读者读的,写了之后可以立刻被阅读,写完一段就能获得读后感,这对作者来说,是极为愉快的感受,一种始终被阅读的奢侈。
直面读者的方式,是西方的经典传统,作者写了一段,习惯是念给朋友听,这也是现今我们很流行的“文学朗读会”的前缘。后来一度改为狄更斯式的“小说连载”,同样随写随发,从写出第一个字开始,直面读者,整个过程都有读者陪伴。民国初年我们不少小说正是这样写的,读者同样会给作者去信,讲自己的读后感。不过,再之后写小说,我们就变为埋首于书斋的一种安静沉默的方式了。
在网上写小说不用真名,同样来自连载的传统,这是一种非常打开的状态。作者仿佛换了一个人,那么愉快又那么迫切地去回忆,这是平常很难有的机会——忽然之间,你所有的名目都消失了,你不再是你。但你又始终在读者的关注下,每天写一节,每一节的结尾处理就会有一种现场感——作者非常紧张,又有高度的表现欲,与读者之间是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虽然《繁花》初稿经过数次改动,但成书后节与节的划分仍然保持了原貌,现在书中的每一节都是当时每一天写的,这同书斋里独自写作时每一节的处理完全不同。
意识到每天的更新文字,始终暴露在读者眼前,那种愉快的程度难以言表。或者说,让你产生出一种超常的谨慎和警敏,调动全身心投入,逼出自己所有的经验和力量,仿佛什么沉睡的记忆都醒过来,进入了一种更安静也更喧闹的状态里,与你的人物故事一起紧密呼吸。最佳的阶段,是你变得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不吐不快,除了赶回家写字以外,没有任何的兴趣。我常开玩笑说,这大概类似怀孕的感受,整个人都不对了,不过是一种幸福。
此外就是闲谈,就是中国传统的“爱以闲谈而消永昼”。我眼中的作者和读者,确实需要这一类闲散的空间。我喜欢博尔赫斯的看法:“正如《一千零一夜》一样,旨在给人感动和消遣。”对读者来说,感动和消遣是阅读最重要的部分,是文学允许的一种方向。记录生活的特殊性和平凡性,是文学永恒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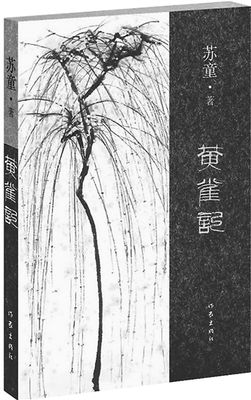
苏童:从没离开这条街
“香椿树街”是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签,我从来没离开过它,从这条街上我时常回头看自己的影子,向自己索取故事。我期望这条街能够延展,能够流动,因为流水不腐。有人担心这条香椿树街会显得狭窄短促,我从未担心过。我描绘勾勒的这条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而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而我要做的,就是让没有喧哗权利的语言,齐心协力顺流而下,把读者送到这条街上来。
好多年前,我熟悉的一个特别腼腆的街坊男孩,令人意外地卷入了一起轰动街头的青少年轮奸案,据说还是主犯。男孩的父母一直声称儿子无辜,为此跑断了腿,说破了嘴,试图让当事的女孩推翻口供,未有结果。那个腼腆男孩多年后从狱中出来,混得不错,性格依然很腼腆,人到中年之后,我遇见过他,有机会刺探当年的案底,追问他的罪与罚是否真实公平,却始终没有那份勇气。
好在有小说。我把他写进了《黄雀记》。
小说里有自由。自由给小说带来万能的勇气,也带来了最尖锐的目光,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探各种人生最沉重的谜底。不过,读者对文字始终是警惕的,充满拷问意识的,当你要模糊“所有格”的时候,他们也许恰好要厘清,那是谁的生活,谁的社会,谁的思想?读者与作家面对一个共同的世界,他们有权利要求作家眼光独到深刻,看见这世界皮肤下面内脏深处的问题,他们在沉默中等待作家的诊断书。而一个理性的作家心里总是很清楚,他不一定比普通人更高明,他只是掌握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技巧。
《黄雀记》里横亘着香椿树街式的伦理道德,人们生活于其中,有真切的温暖与宽恕,有真实的自私与冷酷,有痛楚陪伴的麻木,有形形色色的遗忘与搜寻的方法。当然,隐喻与象征在小说里总是无处不在。《黄雀记》里的人物面对过去的姿态,放大了看,也是几亿人面对过去的姿态。
展望未来是容易的,展望的结果大多化作浪漫的诗篇。而面对过去,最为艰难痛苦的,是自我清算,这无关仇恨与复仇,自我便是自我的敌人。不过,在控告之后,至少还应该反省,至少还有忏悔。反省与忏悔的姿态很美好,那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面对过去的姿态。这个姿态,可以让一个民族安静地剖析自己的灵魂。这个姿态,还有可能带来一个奇迹,让我们最真切地眺望到未来,甚至与未来提前相遇。
版式设计:宋嵩
人物速写:罗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