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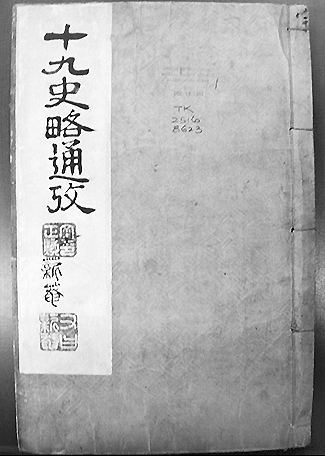


东亚各国部分汉籍
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复旦大学葛兆光和南京大学张伯伟等先生的倡导下,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热潮,这就是葛先生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与张先生所提倡的“异域之眼”。葛先生重史学,张先生重文学,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研究的视角由西方转向东亚,研究资料则是域外汉籍,研究对象依然还是中国本身。这是新世纪的新学术取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
东亚汉籍之价值与研究之必要
东亚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这是因为它有着自身完全不同的特点。德国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时期,几乎同时在印度、西方和中国出现了精神的自觉,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或与之保持差距,或与之有所接触,并被拖入其历史过程。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就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如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汉字、儒教、佛教和法律系统,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汉字则是最为基础的“支柱”,正因为有了汉字,流传下来丰富的汉籍,成为东亚世界共同的财富。亚斯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当我们重新思考中国学术与历史走向时,尤其是在西方理论和话语冲击之下,我们越来越迷失的时候,放眼东亚,发现有如此丰富的域外汉籍,几乎还处于我们主流学术关怀之外,这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失误,也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有所局限,因此,域外汉籍的研究,不仅可以带来新的丰富资料,开阔研究视野,矫正我们认识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中国学术引向一个新的时代。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张伯伟先生在《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都提到过,传统的中国是完全“在中国发现历史”,天朝上国的傲慢使得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周边的历史,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也缺乏一种参照对象,因而不乏片面与偏见。20世纪初所建立的现代学术,则完全是在西方学术体系下建立的,西方的理论既是我们学术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结论的评判标准,尽管它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失自我的学术。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东亚,有着相似的文化观念,历史中彼此共存,文献中记载着彼此,留存下来丰富的汉籍,把东亚汉籍作为研究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拨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迷雾,也可以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从而将中国学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亚汉籍与明清史研究
最近十余年来,笔者一直关注明清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不妨以此为例略作说明。明代发生了一场持续七年的战争——明代抗倭援朝战争(从1592年到1599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是近世东亚所发生的第一场涉及三国的战争,对于中国历史以及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有人说正是因为明朝在这场战争中伤筋动骨,因此战争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就灭亡了,建州女真乘着这个间隙逐渐强大起来,最终取代明朝,成为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研究非常少,除了台湾学者李光涛编过《壬辰倭乱史料》和《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册封日本考》等资料性的著作外,其他真正全面系统的学术论著几乎没有。但是在韩国和日本则有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韩国研究成果甚多,1967年就出版了李炯锡三卷本《壬辰战乱史》,全书2000多页,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题写书名,此后专题研究非常之多,论著不胜枚举。日本研究的著作也十分丰富,以北岛万次、三鬼清一郎、贯井正之等一批学者为代表,出版了系列论著。即便在西方学界,也不时能见到有关这场战争的论著出版。但在我们这边,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至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最近终于有了答案。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与记载就存在问题,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至今仍模糊不清。
首先,明朝史家从来都是把它看成是与万历年间平定宁夏哱拜之役、平定播州杨应龙之役相提并论的“万历三大征”之一,即如茅瑞徵的《万历三大征考》。这就是“从中国历史出发”,而不是具有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去记录这场战争的历史。当时官修的《明神宗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记载一鳞半爪,因为作为天朝上国的实录,记录本朝皇帝起居、本朝政事、制度沿革、官员任免等内容才是最为关键的。即便记载明军在朝鲜半岛的战事情况,也是因为涉及将领的任免与奖赏,才给予一定的关注,而对于整个战争的历程,并不重视,史料挂一漏万,粗疏零乱。
其次,更重要的是,不仅史料错误百出,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也基本错误。只要稍稍将朝方史料与明朝史料对照,会发现即便是同一个人物、同一件事情,记载迥然不同,评价天壤之别。如杨镐,作为壬辰战争的明朝经略,明朝史料把他写成是贪功冒饷的庸才,而《朝鲜宣祖实录》等史料中则处处对他加以称颂,赞颂他是“再造藩邦”的名将。因为《明实录》的编撰者,往往借机党同伐异,甚至颠倒黑白,故意歪曲事实。明朝实录“不实”的问题,不少明代史家就曾加以批评。就杨镐的史事来说,明兵部主事丁应泰弹劾杨镐“贪功冒饷”,但是朝鲜国王、明军总督邢玠、监军御史陈效以及诸多将领,纷纷上疏为他辩白。明廷中因为党争,首辅与次辅的斗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角逐,致使杨镐被罢免。朝鲜君臣则认为这是十足的冤案,可是无法改变明廷的决定。《明神宗实录》的编修,在萨尔浒之战之后,杨镐因萨尔浒战败而被下狱,所以《明神宗实录》在叙述杨镐时,依从丁应泰之说法,且只详载丁应泰疏文,其他材料一概略之。相比其他史料而言,《明实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以后史书依从的范本。以后的史书,无论是《国榷》《明史纪事本末》,还是《明史》《明通鉴》,基本上是因袭《明神宗实录》的说法,或多多少少作局部修补,于是不仅否定杨镐的战功,进而否定整场战争的作用,《明史·朝鲜传》竟然如此论定:“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可是翻开《朝鲜王朝实录》,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
第三,当前中国明史学界对于此次战争的研究,大多以明清史料为主,所运用的史料是片面的,对战争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最终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可见,对于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必须要打开眼界,全面占有各方的资料,充分利用域外汉籍资料,与中国明清史资料,进行互证比勘,去除疑误,消除偏见,才有可能将真正的历史呈现出来。
此外,明清易代史是明清史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除了明清间的战争研究外,对于明清之间的传承,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向来认为“清承明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因为明清之间,既有继承,也有断裂。一定层面上,断裂的因素可能更大些。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东亚的角度来考虑,运用域外的汉籍资料,就可以得出更令人信服的结论。即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两朝的关系上看,断裂的因素远远大于传承,尽管从形式上看,并无太大变化,但朝鲜王朝对明朝采取的是“慕华事大”政策;对于清朝则采取“华夷观”的视角,带有“尊周攘夷”的心态。但是这些资料在中国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却大量存在朝鲜王朝的史籍中,因此域外汉籍资料,不正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吗?而现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的所谓“新清史”热潮,也正是从满文和域外汉籍等文献中,发现许多中国汉籍资料中不存的资料,重新解读清史。他们的结论需加以审视,但是研究视角值得关注。
东亚汉籍与中国史学史研究
域外汉籍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既可以丰富对中国史学史的了解,也可以扩大中国史学史的范畴,甚至重新认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东亚汉文化圈中,史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中国史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古代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几乎每一部重要的中国史籍,都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并且广受重视,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典籍,而他们所编修的史书,也基本上效法中国史书体裁。即以朝鲜王朝为例,朝鲜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完全效法中国史书,只是某些史书中体裁有所变通,如在郑麟趾《高丽史》中,不列本纪而设世家。在日本和越南也几乎类似,日本的《日本书纪》等“六国史”就是模仿中国正史和编年体史编成的,《大日本史》和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也是效法中国纪传体史书而编撰的。但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于这些内容几乎未曾涉及。利用域外汉籍不仅可以弥补这一学术空白,而且考察周边各国传统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吸收与变更,可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史学史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有些中国历史上的史书如今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后,却成为人所共知的重要典籍。即如元朝曾先之编撰的《十八史略》,其基本内容是按朝代、时间顺序,以帝王为中心叙述上古至南宋末年的史事。元明时期,曾作为私塾中启蒙性的历史读本,最初篇帙仅为二卷,后不断经人注释、续编,在元明之际一度流传非常广,并传到朝鲜、日本,成为他们习读历史的重要书籍,至今依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中国,清朝以后则几乎不为人所知,至今在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几乎无人提及。对于这样的史书考察,既可以弥补中国资料的不足,又可以进一步深化中国史学的研究。
总之,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东亚汉籍,不仅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资源,更重要的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野,去除某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迷雾,深入发掘域外汉籍资料,一定可以推进许多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重建新的历史认识,进而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