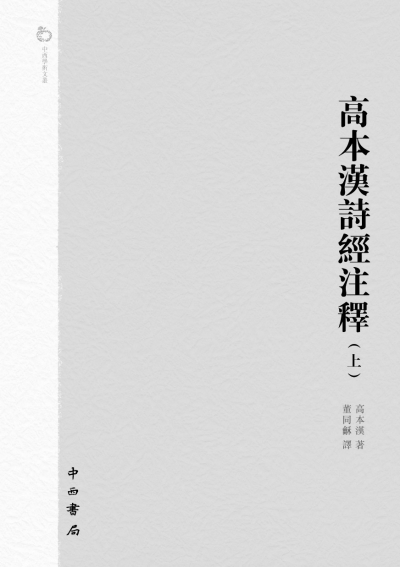
《高本汉诗经注释》(上下),高本汉著,董同龢译,中西书局2012年10月第一版,108.00元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是利用语言学训解古书的一部名著,1960年由著名学者董同龢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但该书在中国大陆至今殊不易见,有感于此,中西书局日前重刊了该书。董同龢先生文亦是一篇名作,在诗经研究等方面深具启发意义,本报转刊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这里译出的是高本汉先生(Bernhard Karlgren)分年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发表的:国风注释、小雅注释、大雅及颂注释,这三部分的注释一共有一千三百多条,译本就合起来称为“诗经注释”。
在国外的汉学界和国内的文史界,高本汉先生的声誉是没有人不知道的。那么,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无须再说了。高氏治诗的动机和方法,他自己在国风注释的序文里交待得很清楚(译本改称“作者原序”),可以看出他是先对中国历代诗学的发展有了深刻的了解,然后才订出目前所应遵循的路线的。至于西方学者研究或翻译诗经的几家,他也都检讨过他们的得失。只是他们的成就较少为高氏所取。但他对于清代学者的批评,却是发前人所未发,而且议论精辟,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
清儒提出了“读经必先识字”的口号。正是因为他们在音韵训诂上有了颇为可观的成就,确能有根有据的认识了不少古书上的字,所以清代学者的经学确能超越汉唐。然而由现代人看来,清儒的音韵训诂之学离开精密的地步实在还有相当远的路程,并且他们运用材料的方法也尽有商榷的余地。高氏特别指出三点:
(一)他们只求出了古音系统的粗略的间架,对古音实值还毫无所知。因此,他们所说某某字古音同,有些地方是靠不住的。
(二)关于字义,他们过于尊崇尔雅、说文等古字典的定义,而忽略许多字在古籍中应用的实例。
(三)引证古书文句的时候,往往三代两汉不分,不去辨别时代真正够早而确能引为佐证的材料和时代太晚而实在不足依据的材料。
这些都是中肯之言。我们更可以说:学问发展至今日,这些话大体上也都是严肃的做学问的人的心声。
我们现在治诗,究竟该如何着手呢?高氏以为:能具体做得到而且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就是比清儒更进一层,客观地求出许多难字难句的确实的意义来。所谓客观,就是尽量汇集诸家的异文以及汉儒以降的解说,应用现代语文学的知识和方法予以抉择,或者另求合宜的新解法。
字义都审定了,通读全句或全章或全篇,有时候还有许多困难。高氏也有详细的讨论。大约那都是我们读古书——尤其是诗经——的先天的难题。高氏提出的句中主语不明和语词缺乏形态变化,本来可以由探求作诗的环境(包括当时作者的心境)来补足。然而三千年前的事,我们可以得而知者才是多少呢?在这一方面,只怕谁都提不出一套具体而有系统的办法来了。
注释作成之后,高氏又有“诗经释文”,分见远东博物馆馆刊第十六和十七两卷。(The Book Odes:Kuo-feng and Siao-ya ,Ta-ya and Sung.)在那个序文里,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类比”(analogy)的办法。他以为:在诗经里,同一个题旨往往在几篇之中大同小异的出现;比较抽绎之后,对每一篇所说的是什么,都可以有些把握来确定;因此,对篇中各句的讲解也就有了帮助。不过他紧接着就警告说:我们有绝对把握的时候还是很少的;在许许多多的情况下,仍然难免见仁见智。
如以上所说,高氏做到的还不是清儒的“读经先识字”吗?他的注释和清儒的“新疏”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把注释读完,便会发现,高氏之所以异于清儒者,在观念上有三点:(一)不把三百零五篇当“经”看,(二)摆脱了诗序的羁绊,(三)不主一家。至于他生当清儒之后,能用清儒之长而去其所短,又有现代的语言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就是在“识字”上,自然是比清儒精密而进步多多了。这可以分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处理材料比较有系统——因为所讨论的都是有问题的字句,所以每一条的注释的第一步都是胪列各家的异文或异说,逐一察看他们是否在先秦文籍中有例证,或者察看在训诂上是否有根据。因为各家的说法都是分项引述和审核,材料虽然繁复,摆到读者面前,都是有条不紊。这种做法当然是纯西洋式的,同时也是我们旧有的“注疏”或“札记”的体裁办不到的。
第二,取舍之间有一定的标准——比较几个说法的优劣,高氏最着重看他们有没有先秦文籍中的实例来做佐证;或者都有佐证的话,又要看证据的多寡和可靠性如何。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说法都可以成立,次一步的标准就是用上下文中相关的句子来对照,看哪一个最合用。如果所有的说法都没有先秦文籍中的实例来作佐证,那就要看在训诂上——或由字形的结构上说,或由本义和引申义来说,或由音的假借来说,又或由他自己所谓“词群”的观念来说——是哪一个说法最合理。训诂上不止一个说法可以讲得通的时候,还是利用上下文的关系来决定。又如果两个说法在他看来都是一样可用的,结果他总是取较古的一个(往往便是汉儒的说法),他的理由是:较古的说法得之于周代传授的可能性多。
第三,处理假借字问题极其严格慎重——高氏不轻言假借。前人说某字是某字的假借时,他必定用现代的古音知识来看那两个字古代确否同音(包括声母和韵母的每一个部分)。如是,再来看古书里面有没有同样确实可靠的例证。然而,即使音也全同,例证也有,只要照字讲还有法子讲通,他仍然不去相信那是假借字。他曾不止一次的批评马瑞辰的轻言假借。他说:中国语的同音字很多,如果漫无节制地谈假借,我们简直可以把一句诗随便照自己的意思去讲,那是不足为训的。又有些三家诗的异文,意义和毛诗的字义相同或有密切的关系,古音则不全同而相近(或者声母只是发音部位同,或者韵母上有或没有介音……),清儒一向都是看做有假借关系的,高氏只把它们当作一个“词群”中的字。关于所谓“词群”,他早在远东博物馆馆刊第五卷有长文论述。这个观念虽然在现代语言上还待商讨,却比我们旧有的“一声之转”是切实而可信多了。
第四,见于各篇的同一个语词合并讨论——例如讨论召南采蘩篇中的“被之祁祁”,就把小雅大田篇的“兴雨祁祁”,大雅韩奕篇的“祁祁如云”,豳风七月篇的“采蘩祁祁”,以及商颂玄鸟篇的“来假祁祁”一并提出。这样互相参照,的确顺利解决了许多不好解决的问题。清朝人也有这样做的,不过不如高氏彻底。
我们可以说,高氏已经做出来的,大体上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人在“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上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是笼统的想了,似乎还没有人具体的筹划过,更没有人像高氏这样脚踏实地的做过。
所谓脚踏实地的做,是指就一本本的书作辛勤严谨而有系统的钻研。以诗经而论,崔述、姚际恒的著作以及古史辨派若干学者的文章不是不足以表现一种进步的学风,然而前者难免欠实在的工夫,后者更都是一鳞半爪。
我翻译高氏这部著作,第一个动机就在于我觉得这是二十世纪中期承历代诗学发展而产生的一部有时代性的书。它固然是高氏的一家之言,同时也确实是诗学在整个学术潮流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表现。
我翻译这部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让有志趣的年轻学者多多的领悟:我们读的虽是古书,而现代的工具和方法又是多么重要。
我读过而又译完这部注释,并没有觉得高氏已能处处臻于完善。这也是自然的。解释全文尽有见仁见智的余地,上文已经说过了。单从认字方面说,像这么繁杂艰巨的工作,一个人在一时也是不能做得尽如人意的。这里不是我个人对这部著作发表批评的场所,而且每个细心的读者当然也会有他自己的看法。只是为提起年轻学者的注意,我倒想把自己见到的,从大处择要提出来。
从材料的搜集来说,如果由我们做,民国以来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诗经字义诠释的文章,一定还要广事采用。上文说,高氏的路线也就是新中国的学者想走的路线。虽然我们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全盘的成系统的做,却也有不少只讨论某一字或某一句的小文章,其中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自然不在少数,都值得重视。
高氏在注释中,似乎始终没有怎么利用语法的观念来做字义诠释的帮助。他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在这方面绝对不是不能。我们宁可说:大概他是十分谨慎,以为古代语法的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不能作有效的利用。其实由我们来看,似乎近人对诗经中若干语法现象的研究也不能说是毫无实在的贡献。有些诗经中虚字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诗经语言结构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诗经的文句是很有些帮助的。再者,如果古代语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对诗经字句的认识自然会比现时易于着手,而且,高氏所谓由句中主语省略和语词没有形式变化而起的困难,那时也许就不是困难了。
关于实字意义的决定,高氏是极端严格的执行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看在先秦古籍中有没有相同的用例。有时候,某种解释只见于某家古注或字典,在先秦古籍中没有相同的用例,虽然由上下文看比较妥帖,他还是不采用。这样好像是有个假定:见于诗经的字在其他古籍一定也有,而且今存先秦古籍就是原有的全部。以常情而论,这似乎是大有疑问的。古注或字典中对某些字的解释在今存先秦古籍中找不到相同用例的,未必都不足取信。古注家讲师承,尔雅等字典多用古籍旧解,错误自是难免。固然不能奉为金科玉律,却也不失为备抉择的资料之一。
和尔雅、说文相反,高氏非常重视杨雄的方言,以为那是西汉口语的实录,代表古语的遗留。我想,许多人的意见恐怕不会和高氏完全一样。
由以上可以看出:我翻译这部注释,并不表示我自己完全同意高氏的每一个说法。清代治诗的几部有名的书都是诗学发展到那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伟著。然而陈奂、马瑞辰、胡承珙诸氏并不尽同;后人也没有谁说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比别人都高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和高氏有相等的学力,下同样大的工夫,另外做出几部诗经的注释,他们必然都和高氏有所不同,各人之间也绝对不会完全一样。这是我们研读几千年前的古书所不能免的。我翘盼我们受了高氏的刺激,能多有几个现代的陈奂、马瑞辰之流的人物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