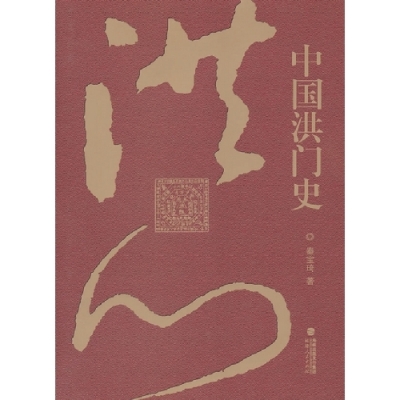
《中国洪门史》,秦宝琦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160.00元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1904年1月11日、12日),太平洋上的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内,“洪门!洪门!”之声不绝于耳,一场庄严肃穆而又热闹非凡的洪门“入闱”仪式正在举行。在舅舅杨文纳、哥哥孙眉的建议下,经过洪门老前辈、“叔公”钟兆养隆重介绍,时年38岁的孙中山正式加入海外洪门组织,并被当场封为“洪棍”(又称“元帅”)。从此,孙中山便被洪门中人视作“自己人”,尊为“孙大哥”。在美洲洪门致公堂总理黄三德的亲自陪同下,孙中山此后在美国的长途旅行和宣传终于获得成效,打开了美洲华侨倾力支援中国革命的大门。
“起共和而终帝制”的一代伟人孙中山,却亲身加入江湖“绿林”组织洪门。这一千古奇闻,不仅大大影响了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人对洪门史(天地会与哥老会)的研究。其实孙中山与洪门的联系自其投身革命之日即开始了。早在他创建旨在反清的兴中会时,其成员中就有很多是洪门兄弟。1895年至1908年间,革命党人在南中国组织的历次武装起义,基本上都是通过两广和海外洪门发动的。后来在全国辛亥“光复”过程中,四川、陕西、贵州、湖南等省洪门也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在边远的内蒙、青海、新疆和西藏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中,也可以看到哥老会的身影。正是基于此,近百年来,传遍海内外、具有很大社会势力的秘密会党组织,引起多方面学者的热情关注,发表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而集其大成者,则为洋洋百万余字的新著《中国洪门史》。
历史研究首重资料,近代史学名家曾深刻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洪门是底层民众自发结成的秘密结社组织,正史官书中所载散乱,洪门内部文献则多隐称夸饰,如何解读才能与档案文献形成互证,成为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中国洪门史》的作者浸淫于洪门历史研究多年,积累了丰富多样而又扎实可靠的资料。早自1974年开始,作者就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尘封的档案中苦心搜集各卷宗中的洪门史料,最终发现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奏折原件,为天地会起源研究中的“乾隆说”找到了核心史据。至于后来作者主编的七册《天地会》资料,更惠及海内外学界,为史学界展开会党早期史研究提供了系统、完整的史料,为洪门史研究者所必备。《中国洪门史》秉承作者注重权威资料的一贯治学风格,利用大内档案、洪门内部《会簿》等一手资料,又兼采清代实录、纪略、方志、族谱、亲历者之回忆录、文人笔记等多种形式的史料。作者尤其注重田野考察,对于洪门史研究中的关键人物和关键资料进行实地考订,务得其实,以订正、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如为了弄清天地会的起源,曾数次远赴福建云霄、东山、诏安等地考察。为探究引起争议的《香花僧秘典》之史料价值,又亲自同周伟良教授前往福建东山,考察苦菜寺当家白云泰所藏香花僧的真本《正源》。其他如加拿大天地会的洪顺堂《会簿》,以及大英博物馆所藏《西鲁序》、《西鲁叙事》、《洪门三十六誓》复印件等,都是洪门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均见书后附录)。正是作者长期的苦心寻觅与艰辛努力,奠定了《中国洪门史》坚实可靠的资料基础。
学术研究以创新为鹄的,但学术创新建立在对该领域的长期积累与不断探索之上,更建立在对前人成果的充分掌握和消化吸收之上。作者数十年来一直专心致力于洪门史研究,先后出版《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洪门真史》、《中国地下社会》等多种专著,成果丰硕,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洪门史研究学者。《中国洪门史》篇首专章详细梳理19世纪末迄至21世纪初关于洪门史的研究成果,详加分析,择善而从,既确保作者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也使本书成为百年来洪门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对天地会《会簿》的深度剖析等等,都是在与其他学者的讨论中不断完善的。书后附录有关洪门史研究的论文、著作索引,更让读者一卷在手,便可对百年洪门史研究的总体情况一览无遗。牛顿说过一句传世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作为从事学术研究四十年的“封笔之作”(见后记),作者这些具有基础意义的工作,实蕴含启迪后学、期盼后人超越前人的学术深意。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这句话,在倡导“经世致用”、“以史为鉴”的中国学术传统语境中,尤其具有“他山之石”的意义。历史学家进行研究,不仅仅要作出史实的因果判断,还要作出史事的价值判断。洪门在清代后期以及民国年间表现活跃,与多种政治势力发生了密切关系。尤其是清末民初洪门发生分化,部分洪门人士积极投身民主革命,也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工具,或者演化成以违法犯罪为主体的黑社会组织,在当代仍不乏影响。而海外洪门则以合法的社团或政党登记注册,成为新时期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因此对洪门立会之由、其团体的性质、各阶段的历史作用等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中国洪门史》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较好地把握了洪门在历史上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的史实。作者对洪门领导底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做了全面、系统论述,阐明了这些起义或起事的积极意义,肯定其在清代底层社会中进行互助和自卫抗暴的历史作用。对于辛亥革命过程中几乎“无役不从”的洪门(两广天地会、海外洪门致公堂和哥老会)的历史贡献,也做了恰如其分的肯定。同时对有些洪门组织进行抢掠、胁迫乃至杀人越货、严重危害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行为,作者亦未予回避,而是秉笔直书,辩证分析。对民国年间洪门的发展、演变也做了客观阐述,以保存史实,供后人资鉴。对清代治理洪门相关律例的系统梳理,既加强了洪门起源问题的分析力度,更为后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总之,《中国洪门史》作者在洪门史研究领域长达四十年,日积月累,故能集其大成。全书资料丰富,考证扎实,故能立其说,“成一家之言”。行文条分缕析,遍采诸家,并将多年来所藏珍贵资料公之于众,故能启其后。孙中山当日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而其时华侨列籍洪门者十之八九,海外洪门实为“华侨之母”。但辛亥革命功成之后,曾经广为联络洪门的孙中山在复蔡元培等人信函中却又声称“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当另编秘密会党史”。民国初年,海外洪门多次请求回国“建党立案”无果,洪门大佬黄三德最终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一对曾共同巡游美国的老朋友彻底闹崩。其中的波澜曲折,或也正是一部洪门历史悲欢离合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