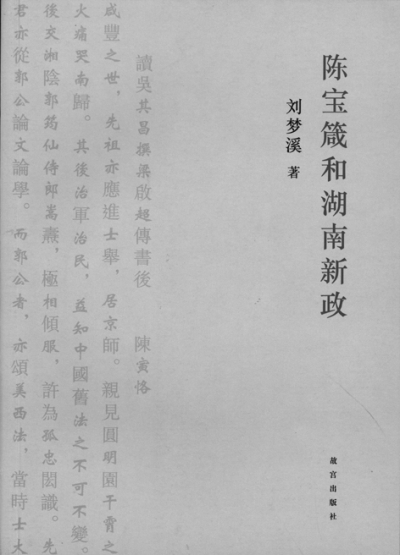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读吴其昌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页167)。
盖寅恪先生所辩者,为其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所主张之变法,乃“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之法者”,而非康有为氏倡言疾行之深涵托古改制意味之变法。两者之不同,为一渐进,一激进。康梁领军之戊戌变法之失败,实系激进变法思想之失败,故为持渐进变法主张之义宁父子所痛心疾首。
察之近现代中国之史乘,戊戌之后的社会与文化变迁,颇有似于激进之“层累堆积”。解者不乏洋务之失在未变法,变法之失在未革命之悖议。故寅老于此吴传后序之结尾处不禁痛乎言之:“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又曰:“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而已。”(同上,页168)
南宋大诗人陆游之祖父陆佃亦北宋名臣,早年尝受经于荆公(王安石)门下,但于安石所推行之熙宁变法未尽应声附和,后司马光“元祐更化”,仍列陆佃入元祐党人碑。俟安石逝陆佃又率诸生前往“哭而祭之”。其于朝政势力分野之无所向背之德范,颇似义宁父子在晚清新旧党争中所处之位置。陈三立岂不言乎:“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故寅老忆及家世,每以放翁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有“元祐党家惭陆子”(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页17)句;1958年作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发慨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诗集》,页130)。
然则寅老所“悲”之“往事”,多为乃祖乃父与戊戌变法及政变之关系者,其“忧伤苦痛”可想而知。
越二十年后之1965年,晚年之寅恪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又以衰病之躯,书写平生唯一之一部家世自传《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特辟专章记述“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再次申明:“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页203)要之,即强调陈宝箴、陈三立所主张之变革为稳健渐进之变革,而非激进式变革。戊戌变法遭遇政变之悲剧,乃操持过切之激进变革之悲剧,为乃祖乃父亦为寅老本人深所不取也。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所谓“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其意其情,其哀其痛,倘在斯乎?倘在斯乎?
因此笔者将陈寅恪先生流露于诗文著述中的此一深层之“哀伤”与“记忆”,视为解开其精神世界牢愁忧结的一把钥匙。而1965年冬日之陈诗《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诗集》,页172),已将此一深层牢结概括无遗,其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之诗句,不啻寅老一生之心路历程并全部著述之主题词。职是之故,笔者于十余年前,经过长时间搜罗爬梳,写就七万言之《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长文,作为陈寅恪研究专书之一章,试刊于2002年出版之《中国文化》杂志。2009年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学报,复经校勘增补至十万字,收入中华书局出版之《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因缘得睹此篇之学界友人,无不以为应单独印行以飨同好云。
盖陈寅恪先生祖父陈宝箴一生之业绩,要以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经由其子陈三立之襄助,所推动之湘省改革功勋最著。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因义宁父子之大义感召,一时间齐集湖南。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创办《湘学报》和《湘报》,开办时务学堂,成立南学会,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但湖南既是改革势力最能发挥的地方,亦是保守势力抵制最顽强的地方。王先谦、叶德辉为代表之反对变革前行之势力,同样极波澜壮阔之盛。故1898年之戊戌变法以湖南为先行典范,同年八月慈禧政变也以湖南所受打击最为沉重。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分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之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们的“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同上)之理想化为泡影。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于京城菜市口,康梁外逃而幸免于难。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皮锡瑞等其余湘省改革人士一例遭受惩处。王先谦、叶德辉诸人则弹冠相庆,王赞叶有摧陷廓清之功,叶许王有力挽狂澜之力。湖南新政在戊戌八月后之凋零景象,有让人潸然泪下而不忍卒观者。
余之所专攻并非乙部之学,因悉心义宁而稍涉晚清史事。故本书之固陋疏误之处,尚祈专门治史之博雅君子多多是正。已往之戊戌变法史研究,不乏及于湘省改革之闳论巨篇,然多以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樊(锥)、毕(永年)等为案例,鲜有从新政的领导者义宁父子之角度据以钩沉研究者。如果此书可从此一侧面补苴罅漏于万一,则幸莫大焉。至于取材运笔之角度,则通过详细梳理甄别所能见及的历史资料,尽量“回到现场”,试图重构当时的人物、事件和故事之互相交错之历史图景。
今恰值辛亥首义一百周年,戊戌之难已过去百有一十二载矣。谨以此书献给变革未竟之21世纪之中国。
(本文为《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自序,标题系编者改拟。该书即将由故宫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