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富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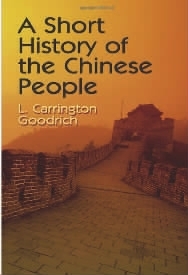
《中华民族小史》英文版书影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出生于通州(现北京通州)一个传教士家庭,并在中国度过童年。他的父亲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曾在中国传教多年,1891年编写过一本北京方言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富路特于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是哥大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的主要建立者。富路特著作等身,最广为人知的是《中华民族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胡适认为它是用西文所写的中国简史中最好的一种(见Pacific Affairs1944年第2期书评),曾多次再版,长期作为美国学生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1930年至1932年富路特为撰写博士论文前来北京进修,住在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华文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日后的美国“中国学之父”)当时也在北京留学,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北京华文学校向富路特请教时,他总是以非常诚恳的态度仔细听我说。从他童年时代在华北的传教士家庭背景来看,他的确可以说已使自己成为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了。仅凭他的博士论文《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就已使他成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中崛起的一颗新星,何况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还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China bound第 135页)1934年富路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富路特在北京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于1935年出版。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重点是乾隆后期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修所发生的文字狱。第二部分是对相关传记、文献、档案的英译。
清朝的文字狱并不始于乾隆。康熙时期就已开始,著名的如“明史狱”和“南山集狱”。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有增无减,著名的如“查嗣庭狱”、“吕留良狱”。为了缓和雍正时期文字狱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和动荡不安,乾隆即位之初一度采取了缓和的政策。但随着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发生,文字狱开始再次爆发。从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富路特在讨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前,对前朝的文字狱也做了简要的回顾,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乾隆大兴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来,“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窜改历史, 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英文版第6页)所以富路特认为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四库全书》 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该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的欢迎,有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Carroll B. Malone书评,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该书同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雷海宗和武汉大学郭斌佳两位历史学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书评开篇时写道:“近年来对于清代文字狱的问题,国人搜集材料与研究的工作虽然不少,但有系统概括一切的专著仍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师Goodrich先生这种勇敢尝试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欢迎。”
在雷海宗看来,富著中有三点是“很动人的见解”:(一)“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二)“无论当初的计划如何,四库的编纂后来成了铲除禁书的一件利器,是无问题的。这一点虽然从前也有人见到,却是一般认四库为无价国宝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复说明并非累赘。”(三)“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
此外雷海宗还认为书后所附《禁书现存目录》(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价值,虽然肯定有遗漏,但在目前“是一个很便利的参考工具”。根据富自己的说明文字,他编制这份目录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目录。他认为要想更准确地做出统计,还应该去查阅包括《图书集成》在内的各类丛书,作为第一份这样的目录,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后人提供基础。根据富路特的初步统计,在乾隆时期禁毁的2600余种书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种。(1999年开始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间的四库禁毁书约1700种)
郭斌佳在书评中也首先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他指出,“吾人觉乾隆朝之文字狱,国人已大概知之。但在西文之中,则完备精详如此书者,实属创见。作者对于中文方面材料,尤以近年我国所出刊物中之有关此项问题者(无论书籍或杂志)均特别注重。读者苟翻阅其卷末之参考书目,即可知其搜罗之广。”确实,在富路特列出的二十七种主要参考书中,除了一些早期文献外,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初的最新成果,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1931—1933年版)、陈乃乾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1932年版)等。
对于富路特在这本书中的观点,郭斌佳也表示基本赞同:“乾隆朝之前半期(自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七一年),作者认为尚无切实禁锢文士之迹,但对于排满思想已渐次着眼矣。作者曾举谢济世、胡中藻、齐召南、齐周华、钱谦益诸案。以为乾隆帝在此时,并无一彻底禁止排满文字之计划,但遇有发觉,则必禁毁耳。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壬辰至戊申),其情形遂大变。乾隆命编纂《四库全书》乘机搜查全国公私所藏书籍。据本书作者之意,高宗并非真欲编《四库全书》,特假此名义,以取缔有碍满清之书籍耳。此种说数,或亦过于偏激,然乾隆之利用机会,取缔许多书籍,则属事实。作者搜罗当时若干圣谕未经刊布者用以证明:(一)地方官吏奉令采访书籍之时,亦奉命搜查排满书籍;(二)在京师选辑四库书目者,同时亦编制禁书目录。故作者之意,《四库全书》之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别有用意存。作者欲证明其论调,列举若干材料以作左证。乾隆欲搜罗书籍,以供检查之意,可于一七七四年之上谕中窥见之(页三二至三三)。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之奏折(页三十三),更可证明疆吏辅佐之态度。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上谕,则说明圣旨更为详尽。总之,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间,吾人随时可寻得例证,证明编纂《四库全书》之双重作用,与其编者之双重责任。”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雷海宗和郭斌佳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问题,特别是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主要在第二部分)。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贰臣传》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富路特将这段话翻译成:
Biographies of this group could not be put in the Ming history, but if they are included in our annals, since their actions deserve mention, along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Fan Wen-ch’eng, Ch’eng P’ing-shih, and Li Kuang-ti, withou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ted, then no clear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英文版154页)
这里的一个大错误在于将“承平时”翻译成了和范文程、李光地并列的人名,而不知道这是和“开国时”对应的一个时间概念。富路特在这样翻译时也显然有些迟疑,特别加了一条注释,说明自己在各种文献中都没有找到“承平时”这个人物的有关信息(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这类翻译错误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因为在雷海宗看来,即使读破万卷书的中国学者“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足的把握”,但多少降低了富书第二部分的学术水准和使用价值。就第一部分和全书来说,郭斌佳认为 “不失为一部博硕之作” 。
富路特的博士论文是在北京写作的,得到多位中国学者的指点和帮助。在“前言”中他特别感谢了袁同礼、马鉴、马准、陈垣、郑振铎等学者。在正文的注释中,他也多次提及中国学者给予他的帮助,如陈垣在1932年5月曾经将自己一篇未刊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借给他参考;1932年7月燕京大学历史教授洪业曾在和他的谈话中说明自己对乾隆禁书意图的理解;燕大国文系教授马鉴曾提示他《清稗类钞》中有关怡亲王收藏钱谦益书籍的材料。
回国后富路特和中国学者一直保持联系,并把他们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英文,最值得一提的是两部:其一是顾颉刚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原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期(1935年7月),译文A Stud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 During the Ming则刊登在1938年12月出版的《哈佛亚洲学报》3、4期合刊上;其二是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原书出版于1923年,英文版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于1966年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