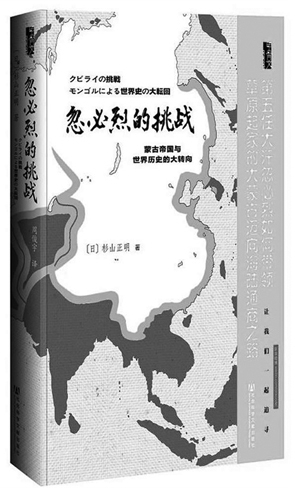
《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45.00元
在这本书中,杉山正明确实也使用了不少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西方史料,但在马可波罗这一问题上,他并没有尽到自己分工的本分——至少对现存汉文史料以及既有学者的研究,他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
最近读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之余,顺着又往下读了罗沙比、杨志玖、尚刚等几位蒙元史相关学者的著作,连带着读了一部分书中辟专章批判的《现代世界体系》。此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反动及其理论上的创建,罗新在《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一文论述颇详。需要补充的是,这本书于1995年在哈佛完成,其摆脱西方中心以及汉族中心的叙事,回归东亚(蒙古)为中心,似乎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端的新清史学派的研究理路有着内在共通之处。近年在美国举行的两次有关元史的国际学术会议,主题都是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认识元代历史,也说明了杉山正明的前瞻眼光。
不过,我更想讨论的是从这本书生发出来的几个问题。首先是《看不见的城市》——杉山正明这本书没读完,我就忍不住将其从书堆里面翻了出来。卡尔维诺笔下的忽必烈汗异常忧郁:他叼着镶着琥珀色嘴子的烟斗,胡须垂到紫金项链上,脚趾在缎子拖鞋里紧张地弓起,眼皮都不抬一下,听马可波罗汇报四方游历所经过的城市。手握无边的权力,他却发现自己的帝国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整个世界正在崩塌。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够让他从绝望的深渊中片刻抽离,依稀看见那些幸免于白蚁啃噬的雕花窗格。
卡尔维诺自承并非专业人士,但他这段马可波罗奉命出使的故事,却并非全然向壁虚造——他的根据是《马可波罗游记》:“当他(马可波罗)出使时,就十分注意依次记下往还所历诸地听到和看到的所有奇闻异事,因而在他回朝时就能够向大汗讲述这些见闻以满足圣意。”蔡美彪和杨志玖认为,马可波罗兼具大汗的使者和斡脱商人双重角色。这个细节在汉文史料中也能得到佐证:1297年,元人虞集在董士选家中遇到忽必烈宫中侍卫,听闻忽必烈曾持续不断地遣使四方,“从容问所过丰凶、险易,民情习俗,有无人才治迹”。(《道园类稿》卷一九)
十四世纪八十年代,马可波罗的手稿印刷成书,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对遥远东方的好奇心。哥伦布读完这本书后深受震撼,他在杭州和扬州等繁荣的商业城市做了记号,并在汗八里(即大都)批下几个字:商机无限。可以说,这本《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人探索东方的热情,间接催生了大航海时代之后沃勒斯坦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此外,它还影响到柯勒律治、卡夫卡、卡尔维诺、布扎迪等人的文学创作。
杉山正明却几乎完全摒弃马可波罗所提供的材料。因为他对这个人是否存在“抱有根本性的疑问”——甚至连《马可波罗游记》是否能够将其视作一本书,他也心存疑虑。在“欧亚世界通商圈”一节,他还不忘提醒“搭上将蒙古贵妃从大元汗国处送到旭烈兀家的使节团船队便船的波罗一家身影只在《百万之书》中可以看到”。相较而言,比他稍早的美国中亚史家罗沙比显得更加谨慎:在《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中,他倾向于认同德国蒙古学者傅海波的观点,即“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杉山正明一再强调蒙古史研究的复杂性和高难度,“有关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文献史料多达二十多国语言”,并以此来讥刺沃勒斯坦在构建“现代世界体系”时,他的“视野里头没有蒙古”。稍后他又着重指出西方研究者处理了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而中日两国学者则主要依据以汉文文献为中心的东方史料做研究这一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分工。在这本书中,他确实也使用了不少波斯文、阿拉伯文等西方史料,但在马可波罗这一问题上,他并没有尽到自己分工的本分——至少对现存汉文史料以及既有学者的研究,他并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
对于马可波罗身份的疑问,也并非始自杉山正明。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就饱受质疑;1829年,德国学者徐尔曼也认为他的游记是一部教会传奇故事;七十年代美国学者海格尔怀疑马可波罗只到过中国北方,到了八十年代英国学者克鲁纳斯干脆就直接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件事,1995年英国学者吴芳思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杉山正明书中对马可波罗的问题如此保守,或许也与八九十年代这股怀疑风潮有关。
据伯希和与穆尔统计,自1351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世的《马可波罗游记》版本多达143种,但原始的手稿早已遗失。吴芳思经分析认为,现存版本有不少后人在原版上添加、篡改的部分。这个问题在中国古籍形成史上也是很常见的,严谨的学者所做的应该是在比对诸文本的基础上,尽量还原出可靠文本,并对其所涉史实进行考订以资利用,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就是一个范例。针对《马可波罗游记》文本中所存在的问题,集大成者是伯希和与穆尔编订的“百衲本”《马可波罗寰宇记》,以及未完稿《马可波罗注》,后经其学生韩百诗整理于1959年出版。翁独健认为伯希和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总括其毕生的学术成果,陈得芝则称之为“最全面、最具权威性”。此外,陈得芝、杨志玖等中国学者对书中涉及到的诸项问题也有诸多讨论、补订。杉山正明贸然否定这本游记,显得过于马虎。比如他书中提到马可波罗护送阔阔真到伊儿汗国一事,就并非仅见于“游记”。1941年,中国学者杨志玖就在《永乐大典》所引元朝《经世大典·站赤门》发现一条公文也记载了此事,其中提到的三位使者的名称与“游记”完全相同。杨志玖据此考证出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在1291年初,这与伯希和注解“阔阔真”条用西方文献所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详见杨志玖《元史三论》)。
杉山正明书中的忽必烈有着超越时代的眼光,以武力为后盾,从地中海到西太平洋编织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水陆贸易网络,其中的核心就是穆斯林群体为主的“斡鲁托克商人”。可是,面对他构建出来的这一套金光闪闪的“体系”,难免让人产生几分建构过度的失真感。真实的历史比杉山正明的描述远为复杂:忽必烈晚年迫于财政压力增税,他的财务大臣回回人阿合马因这一政策产生的冲突被汉人刺杀。比较有意思的是,在汉文史料以及马可波罗的描述中,阿合马都是压迫汉人的奸臣,拉施都丁书写的波斯文献中他却是个促进中国与穆斯林世界贸易的好人,“光荣地履行了丞相职责约二十五年”。据罗沙比描述,整个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忽必烈与穆斯林群体关系一直紧张,甚至敌对。
此外,我比较好奇的是忽必烈的长相,可惜杉山正明这本书中没有配插图,好在罗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中有不少,恰好可以佐证西方人对忽必烈的想象。在伊儿汗国宰相拉施都丁主持编纂的《史集》手稿插画中,忽必烈是一幅伊斯兰人的形象;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波罗兄弟觐见忽必烈》,他高鼻深目,俨然欧洲帝王;比较符合真相的是刘贯道1280年《出猎图》里面的形象,65岁的忽必烈身材肥硕,和《马可波罗游记》中“筋肉四肢,配置适宜”的描述相去甚远。
1798年,大烟鬼柯勒律治批阅《帕切斯游记》,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围墙”时睡去,梦中文思泉涌,作诗二三百首,醒来后记忆清晰,正拿笔誊录,忽然有客来访被打断,只留下54行的残篇《忽必烈汗》。这是杨德豫先生翻译《柯勒律治诗选》注释中的一个小故事,行文至此我实在忍不住将其摘录下来,因为我也曾有过柯勒律治般“梦中诗千行,醒来全忘光”的悲惨经历,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