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仲殊著《三角缘神兽镜和邪马台国》日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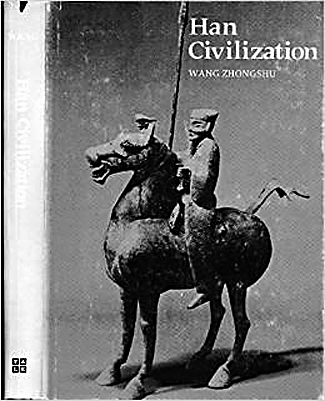
王仲殊著《汉代文明》英文版
新近面世的《王仲殊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荣誉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仲殊70余篇学术论文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内容厚重,其中许多涉及汉唐考古和中日考古比较研究的成果,已经被学界视作经典。
王仲殊的治学特点之一,和一些前辈考古学者同样,即以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熟悉和理解,作为推进考古学的重要条件。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之说,中国古史研究者逐渐重视文物考古资料的运用。而考古学的进步,其实也需要在发掘地下文物的同时,注重发掘传世古籍中的重要文化信息。王仲殊早年有丰厚的文献学知识的积累,又有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学术背景,正是以此为基础,结合承夏鼐先生指导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实践,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优势。例如,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等论文,都较早提供了图像文物与文献记载完好结合的研究方法的范式。《汉长安城宣平门的发掘》作为发掘简报,也充分利用了诸多文献所见汉长安城史料。王仲殊曾经说:“考古学研究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在历史时代考古学的研究上尤其如此。中国古代文献浩如烟海,自当按个人的专业需求,择要阅读。要紧的是必须懂得文献史、目录学等,以便在繁多的古籍中寻求确切相关的记载,加以考核。在引用文献记载时,务必实事求是,力求准确,不可断章取义,切忌牵强附会。”《王仲殊文集》收录的许多论著,可以为后学者提供路径的引导和实践的榜样。
历史学门类现在已经分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这样的划分固然有许多好处,但是如果简单地绝对地相互分断,彼此割裂,显然又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王仲殊文集》对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考古学三个专业的学人均可以提供指导和启示作用。特别值得提示的,是王仲殊对于中日两国古代铜镜比较研究、中日两国都城和宫殿形制比较研究,以及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关系研究等学术方向的收获。在王仲殊的学术功业中,这些论著既体现了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也对于世界史研究有重要的推进。比照“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论定日本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为真品,是确定可信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实证。对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经认真考论,判断为东渡的中国工匠在日本铸作,而并非中国魏朝皇帝所赐,亦非乐浪郡产品。这些研究成果,以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宫内大极殿龙尾道与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的形制的考察,关于唐长安城圆丘对日本交野圆丘的影响的说明等,也都既提出了考古学的新识,同时也澄清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若干重要疑难问题。
王仲殊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视野,除中国古代文明遗迹外,及于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甚至远至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等地。他还曾经发表日文、英文考古学论著。王仲殊和他的学术同事们的相关工作,使得中国考古学得以面向世界。王仲殊先生曾经谈到中国“考古学大国”的地位。他说,“毋庸置疑,中国是考古学大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中国考古学,这当然是好事。中国学者在研究本国考古学的同时,也应适当地研究外国考古学,其中包含中外交流考古学。这样,我们的国家更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考古学大国。”收入《王仲殊文集》的一篇访谈录题名《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其中又明确提出了“汉唐考古学国际影响深远”的理念。他还在另一次访谈中提出,“年青一代的考古学者应该有‘兼通世界学术’的抱负”。现今一些中青年考古学家的工作计划中已经列入外国考古学的任务,首先是丝绸之路沿途以及中国文化曾经辐射影响的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王仲殊的研究方式,可以看作能够指引这些工作取得进步的有益的向导。
《王仲殊文集》 王仲殊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