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又是一年祭扫之时。近日,澎湃新闻专访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华教授请他谈谈清明祭扫传统所承载的中国礼仪文化。
杨华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中国文化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礼制方面的研究,注重经学与史学、简帛与礼制结合互证的研究,2021年其新书《古礼再研》(专著)、《中国礼学研究概览》(主编)等先后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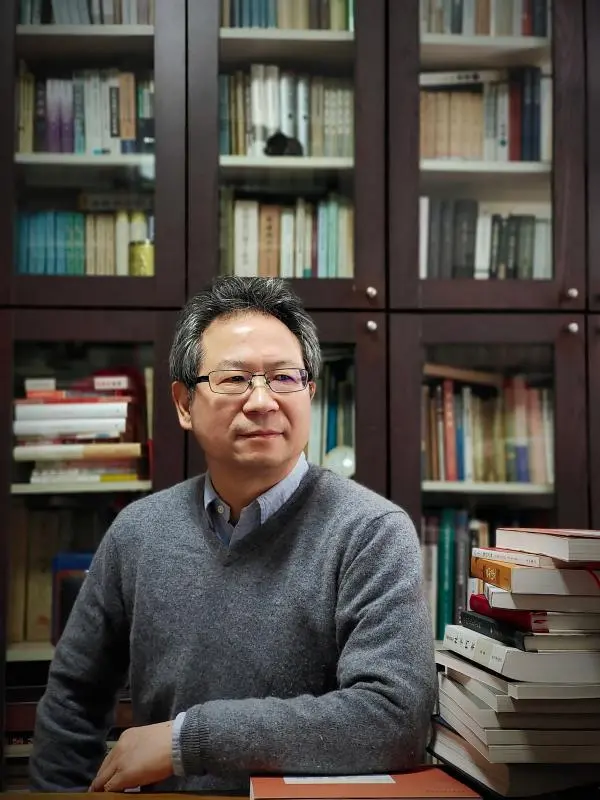
杨华
澎湃新闻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以扫墓祭祖为主要活动。请您谈谈清明的祭祖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杨华:这个问题说起来很长,可分两部分说,一是清明扫墓的来历,二是墓祭的传统。我先简单回答第一个问题。
其实,上坟墓祭一直被视为劣俗,与儒家正礼主张的庙祭互相冲突。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反反复复,唐代玄宗时期干脆将寒食上墓的民间习俗编入五礼,成为正式的国家官颁礼式。开元二十年(732)四月二十四日,皇帝敕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90年后,唐穆宗长庆三年(823),进一步颁布法令,不得阻碍官员出城扫墓:“文武百官,有墓茔域在城外并京畿内者,任往拜扫。但假内往来,不限日数。”后来朝廷还规定,按照做官的年份,满五年可以请假之类。这样,寒食扫墓就有了法律保障。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一诗对清明扫墓的情景有真切描述:“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青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风雨人归去。”他看到的寒食扫墓习俗,与今天已经差不多了。
寒食节来源于“改火”,古人在不同季节改用不同的木材(如榆、柳、杏、枣之类)钻木取火作为火种。交替时期则要熄灭旧火,重生新火,以便去病消灾(古人认为使用烧得太久的火会引起疾病),促进农作物生长(烧荒播种),中间有几天要吃寒食冷饭。这是春夏之交寒食节的由来,介子推故事只是个传说而已。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目前所知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见于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实际上可能更早,可上溯至周代。清明与寒食这两个时令,在时间上重合,其文化功能也相近,于是演变为清明祭祖。

2022年3月20日,成都凤凰陵园,清明节将至,市民提前扫墓。
澎湃新闻
:这一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容易,但回过头讲墓祭,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
杨华:是的。中国人的祭祖传统非常久远且从未中断。在商代甲骨文中,有一套系统化的“周祭制度”,即普遍而循环的祭祀体系,一年36旬都在按顺序地祭祀先王先公。周代青铜器,经常整个窖藏被发掘出来,多达几十件,现在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有人认为可能与祭祖的仪式有关。在这些青铜铭文中,常常记载一个家庭几代祖先的功绩。例如,1976年在陕西扶风发现的《史墙盘》,有284字铭文,记载了微氏家族5代祖先辅弼6代周王的史事,显然是追享祖先、祭祀祖先的产物。金文中有大量的嘏辞,就是祭祀时那个代表祖先的“尸”对参与祭祀的子孙们所说的祝愿之语,与《诗经》等文献可以对证。“追孝”“追享”“孝享”都是金文中的常见语汇,就是指在庙中进行祭祀活动。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祭祖活动就是在宗庙中举行。在汉代之前,庙祭时有一个人扮演祖先,叫做“尸”,即尸位素餐的尸。他从祖先的孙辈中选出,代表祖先接受供奉,吃饭饮酒然后让祝官转诉嘏辞,即祖先保佑子孙的美言。上古中国,一个祖先一座宗庙,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这是指他们供奉祖先的代数。汉代以后,用活人扮演的尸祭不流行了,改为木制或石制的牌位来代替祖先。同时对祖先神也改为合祭,不再单独修庙,多代祖先就同在一个屋子里了。
中国古代是否举行“墓祭”,即到墓前祭祀祖先?首先必须思考,古人埋在哪里?有没有坟墓?夏商周时期,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流行的竖穴土坑墓(向下垂直挖掘墓穴),只有关中西部的秦人有一些洞穴墓,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有一些土墩墓。一般说来,战国之前的埋葬习俗中,没有墓上建筑。连孔子都不知道他父亲的埋葬之处,“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周易·系辞》也说上古丧葬是“不封不树”的。连先人埋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进行墓祭呢?只能在庙中祭祖。
寝、庙、陵、墓是四个空间,不了解的人常常会弄混淆。寝是寝宫,即死者生前居住的地方,墓是他死后埋葬的地方,庙是祭祀祖先神的地方,这都很清楚。最不好理解的是陵。古人曾经指出,“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汉代以降,帝王之墓才称为陵。实际上,早在战国后期赵、楚、秦等国就开始流行陵园之制。战国晚期中山王墓还出土了一块长宽分别为94和84厘米的铜版,叫“兆窆图”(兆域图),画的就是中山王的陵园平面图。里面有五座大墓,堆土墓就是当时流行的高台建筑,上面盖有房子(称为“享堂”),周围有几层围墙。面积广大、封土壮观的秦始皇陵上,同样也有宏伟的廊庙楼宇,与它周围的多种建筑合起来成为一个大陵园。这种陵园里也设有寝,陈设着死者生活用品、家具和卧具,并住有宫女,如同其生前一样侍奉。“事死如事生”,死后把他生前的寝也移到陵园,这就是陵寝。
战国后期以降流行的制度,可以概括为“陵园起寝,陵庙分离”。西汉初年,城内的庙与城外墓地的寝相隔较远,刘邦的衣冠就陈列在墓地陵寝中。每次祭祀时,都要将它拿出来,通过一条“复道”(汉人称之“衣冠道”),运到城内高祖庙中去享祭,这个礼制活动叫做“游衣冠”(因为当时人相信,死人之衣冠上附着死者的灵魂,如招魂礼即“复”礼便用此)。因距离较远而不方便,后在叔孙通的建议下,汉惠帝在靠近陵墓之旁另建了一座“原庙”。这样,陵便与庙结合起来,成为定制。从陵上起寝、陵庙分离,演变为陵旁立庙、陵庙一处。这一转变过程,可能始于战国,而完成于秦汉之际。对死者(近祖)的祭祀,转移到城外陵园;城里的宗庙功能大为缩小,由于君权扩大,其政治功能被剥离到朝堂上,只是用来定期祭祀远祖和举行王族内部事务礼仪活动了。巫鸿先生把这种变化概括为,“祖先崇拜中心逐渐由宗族祖庙迁至家族墓地”。
关于中国上古是否存在墓祭,其实历来礼学家都有很多争议。东汉的王充、蔡邕,三国的魏文帝,清代的顾炎武和徐乾学,现代学者杨宽等,都认为“古无墓祭”,只有庙祭。清人赵翼则认为,中国古代早就有“上冢之俗”,因为下层人无财力建庙祭祀,只有到墓前祭祀,“庶人之家不能立祠,则祭于墓,相习成俗也”。晚清以来,这种观点越来越流行,孙诒让、吕思勉等学者都持此说。近年来,由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上古存在墓祭的观点更多了,钱玄、尚秉和、杨鸿勋、李伯谦等学者都主张,先秦早就有墓祭的传统。并找到不少证据,例如,商王大墓周边有很多身首异处的祭祀坑,西周晋侯墓地有血祭坑,春秋中期的秦公大墓有墓上建筑。也有学者对这些证据提出否定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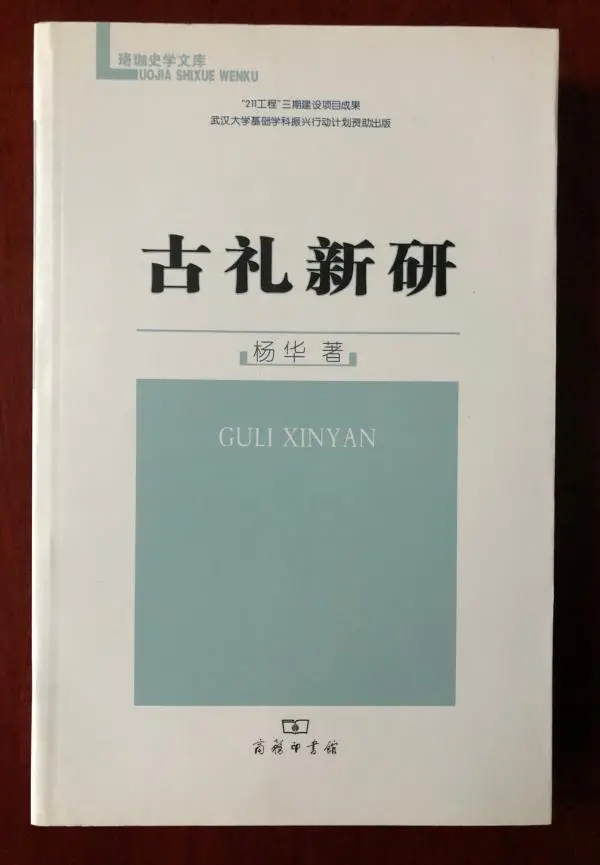
《古礼新研》,杨华著,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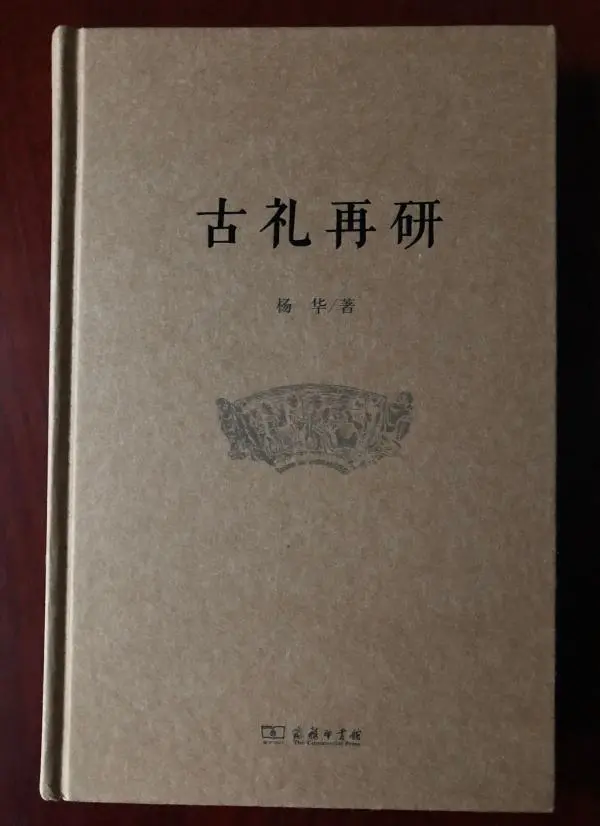
《古礼再研》,杨华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我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战国时期,《商君书》《吕氏春秋》等文献的记载都可以作为证据。《周礼·冢人》记载,冢人之职负责管理族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也就是说,通过坟墓的大小及其上的标识来区别贵族的等级高低。东汉时郑玄注说“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臣曰封”,并举了汉代通用的《汉律》为例:“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这无疑与西周春秋时期的“不封不树”大相矛盾。一般认为,《周礼》的年代较晚,甚至有人认为是汉代的伪作。我们觉得,它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史事,应当没有问题。考古发掘也证明,战国时期有了很多封土墓,现在湖北有很多“冢子”,就是楚国高级贵族甚至王族的高坟大墓。1970年代出土的中山王墓也是封土大墓,支持了这种说法。对于战国封土墓周边是不是有祭祀的痕迹,考古界此前很少留意。据说2002年在九连墩大墓的发掘中,发现墓前灰坑,但相关报告至今未见。不过,新出的秦简已经证明,秦汉都有“祠墓”、“上冢”祭祠的说法。例如,放马滩秦简《丹》篇(或称《墓主记》《志怪故事》):“祠墓者毋敢哭。哭,鬼去惊走。”北大收藏的秦简《泰原有死者》内容与之大致相似,也说:“祭死人之冢,勿哭。须其已食乃哭之,不须其已食而哭之。”《悬泉汉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上冢不欲哭。哭者,死人不敢食,去。”这些都说明,在秦国或秦朝已有坟前墓祭的礼俗。
而正史文献中,记载中国的“上陵”传统,则是始于东汉。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正月,皇帝率领百官朝于其父皇光武帝的原陵,此后各朝,便兴起“上陵”之礼,庙祭正式转变为陵祭(墓祭)。在这条材料的注释中,引证了东汉应劭所著《汉官仪》,说自秦朝以来,每逢月底、月中、二十四节、伏日、社日、腊日和四季,守陵之人就要为死去的帝王“上饭”。可见早有此俗,只不过汉明帝把这一习俗礼典化了。所以,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说:“古礼庙祭,今俗墓祀。”
澎湃新闻:祭祖传统与古人的生死观念直接相关。古人在丧葬礼仪上既讲“事死如事生”,又讲阴阳两隔、生死有别。可否请您展开谈谈这里的“如”与“别”?
杨华:确实如你所说,这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事死如事生”容易理解,对此有好多礼制规定。例如,居丧期间孝子不能从东阶(阼阶)上下,因为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一家之主,他是从东阶(阼阶)上下的,于是自己只好由西阶上下。又如,一个人平时出差远行,要举行告别之礼,叫做“祖道”。那么他死后下葬时,也要把棺柩抬到宗庙,举行“朝祖”之礼,即举行一场死者的告别远行仪式,《朱子家礼》说:“此礼盖象平生将出,必辞尊者也。”又如,父亲平时活着的时候,孝子“出必告,反必面”。那么父亲死了,对待他也要“出必告庙,反必告至”。祖先虽然不能活着听你汇报了,但在宗庙里作为神在听你汇报。这就是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整个祭祀礼仪中,都假定被祭祀的祖先会前来享祭,并与我们同在。从斋戒、杀牲、迎神、献神(献食、献酒)、送神等一系列过程来看,每一步骤都是要做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然而,古人又特别讲究生死之别。例如,“死者北首,生者南乡”,活人平躺时与死人头向相反。又如,古人平时席地而坐(实即是跪),为了舒适不倦,需要一个搁放手臂和倚靠身体的“几”,类似于窄而长的小板凳。为客人布席时也要设几,安放鬼神时也要设几布席。礼制规定,“设神几皆在右,为生人皆左几”,生者与死者设几的位置要完全相反。又如,平时行拜礼时,也是吉拜以左手在上,而丧拜则以右手在上。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总之,生与死礼仪相反。古人无法讲清为什么,一概以阴阳相别来解释。例如,清代赵翼就认为,“生人阳,故尚左;鬼神阴,故尚右”。
我认为,这与中国人对待死者的观念有关,反映了古人对于鬼神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希望得到祖先的福佑,对之极尽虔诚恭敬之能事,另一方面,又担心祖先化作鬼神之后返回阳间作祟,给我们造成麻烦乃至灾难。中国古代有一种埋入坟墓的文献,叫做“买地券”。券文中经常会写“死生异处,不得相防”、“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泰山”、“千秋万岁,莫来相索”之类的句子,意思是说,凭着丹书铁券为证,人死之后阴阳两隔,死者不得再返回阳间来叨扰生者、追索债务。我曾经指出,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除了《左传》等传世文献之外,云梦秦简《日书》中有“某某为眚”的祷辞,其巫术就是占卜出谁在作祟而导致你生病,例如“外鬼父世为眚”、“母世外死为眚”、“王父谴牲为眚”、“外鬼父世见而欲,巫为眚”。孔家坡汉简中也有“患大父”、“患高姑姊妹”之类的句子,也是说他的某个亲戚让自己生病了。战国包山楚简也是如此,通过占卜发现,墓主的四代亲祖在“为祟”,令墓主致病或升迁受挫,于是对之采取克制巫术。而东汉时期的简牍材料《序宁祷券》中,也有“天公所对,生人不负债,死人毋谪,券书明白”的句子,后来道教吸收了这种巫术。总之,中国古代的祖先鬼神,向来具有两面性,一是佑人以福,一是罚人以祸。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所以才有了对待生者与对待死者截然相反的做法。《仪礼》说,为死者下葬准备的器物,叫做“明器”(冥器),实即“鬼器”。这些鬼器的特点是:“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下葬时,竹器编成而无边缘,陶器做成而无光泽,木器做成而不加雕凿,琴瑟做成却不能弹拨,竽笙做成却不能吹奏,陪葬钟磬却不给它做悬挂的架子。这些明器的目的在于把死者当作神来看,神是我们活人所不能捉摸的。正如郑玄所说,“言神明者,异于生器”。明器的根本特征,是与生人所用之器不同。汉代人把死亡称为“物故”,其解释非常直接:“物,无也;故,事也。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这个人不会再使用这些器物了,这就叫做死亡。《礼记·檀弓》说,孝子对待死者的态度非常矛盾:如果完全认为他毫无知觉,那是不仁的(“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如果认为死去的亲人确实还有知觉,那也是不智的(“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这两种态度都有问题,于是采取折衷的办法,埋葬时所做的明器,既能成形,但又不能真正使用。在商周考古中,常常见到“碎器葬”礼俗,即把兵器、食礼、乐器故意打碎了埋进墓中,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后代丧葬还在沿用这种习俗。尤其是折弯、打碎兵器后再随葬,恐怕就是担心他重返人间持兵为害。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祖先神就怀着矛盾心态。既戒慎恐惧,战战兢兢,虔诚洁净地进行祭祀;同时,又采取各种方法,让死者的器物、神位、方向与现实中的我们截然相反,以免他会重返人间“相索”“相防”,加害于我们。或许,这正是祖先崇拜的宝贵所在,它令我们有敬畏感和上进心,让子孙们努力为善去恶,成就功业。
澎湃新闻:如您所说,庶民之礼只是后来才被纳入到国家视野之中的。以今天来说,一些有点年纪的人对于殡葬的门道可能也是知之甚少,转而由专业人士去操办。传统时代礼仪从制度到日常是如何落地的?
杨华:中国古代礼制是为上层社会设计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规则,在先秦到宋代它都服务于皇室和贵族,平民之礼基本不受重视。宋代以后,才有所谓“通礼”,即把庶民之礼也纳入国家制度的视野。在平民社会中推行礼仪,这得归功于司马光、张载、朱熹等人。他们让下层平民也学会贵族的生活样式,这算是礼制的“下移”;他们让全社会不再像魏晋隋唐时期那样,按照佛教的节奏过日子,这算是本土儒家礼制的“回归”。为此,他们制作了很多儒家礼仪的简本,以向社会推广。其中最流行的当然是《朱子家礼》了,它影响了最近八百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按照先秦《仪礼》,丧葬礼仪包含了几十道环节。根据其简化版《朱子家礼》,大致可以分作以下三个阶段:(1)临终和始死。包括死于嫡室(正寝)、举行复礼(招魂)、初步处理尸体、始死上奠(供品)、讣(赴)告、为铭(悬幡写“某氏某之柩”)、浴尸、饭含。(2)殓尸和成服。死亡第二天小殓(在室中为死者穿衣),第三天大殓(在堂上将尸体入棺,填充棺材),成服(按五服关系分别穿丧服),各入丧位居丧。(3)入葬和葬后。择日、穿圹(挖墓)、朝祖(告别祖庙)、遣奠、发引(柩车出发)、下棺、下墓志、题主(题写神主牌位)、反哭(回家在神主牌位前哭祭)、虞祭(安魂祭)、卒哭(丧礼结束,转为祭礼即吉礼)、班祔(死者牌位按顺序归入祖先神位行列)、小祥(周年祭,第十三个月)、大祥(二年祭,第二十五个月)、禫祭(第二十七月)。

影视剧中体现的复礼(招魂)以上程序,大致保留了《仪礼·士丧礼》的程序。今天看来相当繁琐,但实际上它对上古贵族的丧葬仪式已经进行了极大的精减和简化。例如,《士丧礼》规定小敛衣裳19套,大殓衣裳30套,另加明衣1套、袭衣3套,共53套裹在或盖在尸体上,而《朱子家礼》取消了这些规定。上古的“殡”与“葬”是两个程序:大殓后在家中“殡”,即把棺柩放入西阶上挖的浅坑,涂上泥巴,象征性地埋一段时间(士三月);到葬日,再启出来,朝祖然后埋葬,是谓“葬”。但朱熹的《家礼》中取消了殡这个环节:“今或漆棺未干,又南方土多蝼蚁,不可塗殡,故从其便。” 《朱子家礼》关于丧葬的规定,非常细致。小到棺材和神主的尺寸、墓室的大小、防虫防水的措施、告神和墓石的文字,等等,均一一注明。
朱熹不是腐儒,他制礼时向来讲求“礼时为大”和“通变实用”。在《朱子家礼》中,可以看到很多“从俗”的内容。例如,原始儒家中并没有焚香的仪式,这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带给中国的仪式,但《朱子家礼》中在发引和虞祭时,都有焚香环节。又比如,《礼记》等文献中说,天子七日而后殡,停尸七月而后葬;诸侯五日而后殡,停尸五月而后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后殡,停尸三月而后葬。司马光、二程和朱熹都曾对这种久丧习俗加以反对,他们当然不好直接批评儒家礼书,而说这是世俗根据阴阳禁忌而择日的恶果:“盛夏之际,至有汁出虫流,岂不悖哉?”在《朱子家礼》中,对于民间流行的看风水、择葬日,他也没有过多反对,而是说“且从俗择之可也”。
《朱子家礼》还反对两件事。一是久丧。当时民间丧家常常把尸柩放在寺庙,交给僧人看管,往往经年累月,甚至数十年不葬。朱熹认为,这要么会被盗,要么被僧人抛弃,“不孝之罪,孰大于此”。二是厚葬。他认为下葬时只要用死者衣物把棺中“务令充实,不可摇动”即可,世俗恶习喜欢把金玉珍玩放置棺中,这既“启盗贼心”,又成为“亡者之累”。他一再强调要“相时量力而行之”,坚决反对为办丧事而破财、毁家、伤身。
《朱子家礼》在中国已流行七八百年了。明清时期,各地制作或刻印了多种《家礼》,乡村涌现出大量礼生,以帮人办丧事为业,实际都是以《朱子家礼》为蓝本的。这期间,当然还有佛教、道教,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今天,中国人的殡葬过程就是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同时融合其他元素的礼俗文化。中国人的所谓“老礼儿”,也是大致如此。各地殡葬习俗可能各有不同,只不过截取或者保留了这个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而已。例如,各地都讲披麻戴孝,这无疑是上古和中古以来“成服”环节的变异;亲人亡故的讣告、慰问丧家的启状,在《朱子家礼》中都有固定写法,旧社会的媒体中还有所见。当然,今天也有大量的殡葬仪式与旧礼不符了,例如,花圈就不是中国原有的祭奠形式,在手臂上戴袖章也不是,开追悼会和念悼词也与中国古代的丧礼不同。至于今天通行的火葬,则更是佛教的殡葬形式,司马光、朱熹等人都曾大加挞伐,视为“不孝”。明清朝廷甚至立法,严惩焚烧亲人遗骸的不孝行为。
今天流行的殡葬仪式,已是儒、释、道、耶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元素的杂糅,要想再捍卫或者恢复儒家丧葬礼仪,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生活节奏异常忙碌的今天,人们往往把丧事交给殡葬公司,即所谓“一条龙”服务。全世界都是如此,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但我认为,无论是丧家自己主导,还是由殡葬公司操办,都应当注意几条原则。第一,尽可能地保留和尊重传统老礼,尤其是那些无良的殡葬公司,不要自创很多无谓的庸俗仪式,以谋取钱财。第二,学习朱熹等儒家精英的丧葬理念,从俭从速,坚决反对厚葬久丧,反对大操大办。第三,要尊重亡人的意愿,提倡殡葬的多样化。火葬、土葬、水葬、林葬、天葬都应当尊重,值得提倡。第四,保护环境,提倡不留痕迹的自然葬法。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死者的骨灰都实行“固化”即水泥化埋葬。水泥墓穴的自然降解需要几百年,石制墓碑更是永久存在。目前各大城市周边,都被多个公墓陵园包围,这些无法消除的“亡人家园”已经到了与生者争抢土地的程度。从法律层面改变殡葬习俗,切实保护自然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杨华主编,武汉大学2021年4月出版
澎湃新闻
:当下中国社会老龄化日益突出,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形式,社会也更提倡厚养薄葬。在养和葬的厚薄上,传统礼制有怎样的讨论?
杨华:中国传统孝道包括几个层次。第一是孝养,即在物质层面保障父母,让老人吃饱穿暖。第二是孝敬,即在精神层面敬重父母、顺从父母、娱悦父母,“无违尔志”。第三是“承志”,即在父母死后,继承遗志,光宗耀祖。儒家将其总结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前两个层次,老人都能感受到,享受到,但第三个层次则不然。人死后无感,他当然无从知道后人的所作所为,但孝子为什么还要“祭之以礼”,仍然要一如既往地继承遗志?
原来,这些针对先人的祭礼和孝行,并非做给祖先看的,实际是做给同辈和后人看的,目的在于“教化”。通过这些行为,令后辈今后也这样对待自己,而不是敷衍乃至欺骗自己。往大处说,令后辈努力上进,光宗耀祖,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入华,每当此时,常常被贬斥为“无君无父”,大受抵制。这是中国儒家精英的总结,也是下层民众的普遍认识。范文澜曾经总结说:“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惟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特征之一。宗教在汉民族不能生深根,宗法是起了抵抗作用的。”
孔门弟子中,曾子最讲孝道,他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待祖先的态度实际上决定着当代社会的民风。《礼记》中说,荒废丧祭之礼是“倍死”,实际意味着“忘生”。我们认为,对死者的“追孝”,其根本目的还是要落实到对生者的孝行。如果父母活着时没有尽到义务,死后的丧祭之礼无论多么排场,也是徒劳。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孝道的行为规范和教化措施。其一,全社会有完整而细致的养老礼俗。比如,《礼记·内则》说,“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老年人受到的优待逐年增加。七十岁致仕,七十以上不再为人服丧。六十岁提前一年准备送终之具,七十岁提前一个季度,八十岁提前一个月,九十岁提前一天。其二,平时孝子侍亲有一套礼制。例如,孝子随长者出行时要“必操几杖”,要循着老人的目光方向,随时备问。平时要早晚清安,让父母冬暖夏凉。父母健在时要保全己身,不登高,不临深,让自己处于危险就是“不孝”。父母生病时,要展现哀戚和节制享受,“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这些礼仪细节,不胜枚举。其三,历代的家训、家礼和乡规民约,都保证了传统孝道的传承不辍。所有家谱中都有关于孝道的记述和训诫,曾国藩家书就说:“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各地有大量的乡约,都强调定期聚会,互相督查,彰善惩恶,实际上通过邻里之间的臧否物议,把不孝行为抑制在萌芽状态。其四,古代还有很多教化措施,比如科举文本的学习、民间善书的劝诫、各种宗教的禁忌,都让孝道深入人心。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有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让“不孝”成为实实在在的罪行,使不孝子孙受到惩罚。云梦秦简《封诊式》和汉简《二年律令》规定,子孙杀死父母、打骂父母和祖父母,要枭首弃市。教唆他人不孝,也要判刑。《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 、谋大逆、谋叛 、恶逆、不道 、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是绝不容赦的死罪。古代法律讲求“同罪异罚”,对亲人犯罪的惩罚力度,要超过对他人的犯罪。有几种现象是极大的“不孝”,一是“匿不举哀”(不报告亲人死亡而悄悄埋葬),二是“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在服丧期间褪去丧服悄悄享乐),三是“冒哀求仕”(为了做官而隐瞒亲人死亡),四是“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服丧期间婚娶和生子)。另外,最让今人诧异的是,秦律规定老人只要申告子女“不孝”,官府就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要处死(“谒杀”)。但是,有时候老人已经昏聩糊涂,没有理由地诉告子女“不孝”,于是汉代法律规定对之有所修订,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必须“三环(宥)之”,即在清醒时连续上告三次,官府才予受理治罪。总之,中国古代通过软和硬两方面的措施,使孝养落至实处。今天,我们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有遗弃罪、虐待罪和其他保护老年人的条款。但是,由于家内犯罪不易界定、不易取证,如果没有关于孝义的道德自觉、没有关于孝道的礼教内化,要在全社会提倡孝道、落实孝道,仍然有相当难度。
今天,中国早已进入老年社会,老龄事业正蓬勃开展。不过,全社会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代际关系的交流仍然在家内展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孝养传统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